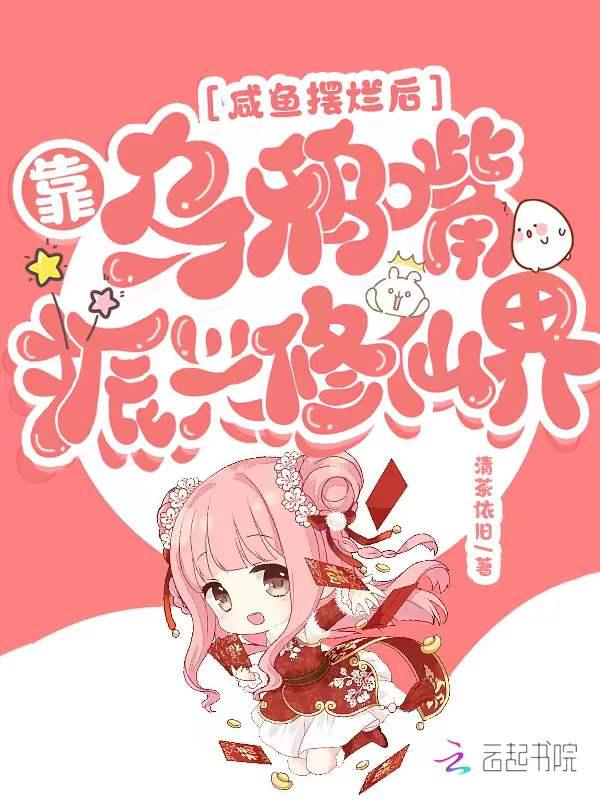52格格党>夫郎赘婿又在硬饭软吃 > 第458章(第2页)
第458章(第2页)
“孩子四岁了,在府外头,跟着他爹学手艺。”
“不知大哥是做什么手艺的?”
喻石榴笑了笑道:“会些木工活,做些小玩意在集市上卖一卖。”
“原来如此。”
温野菜熟练地搓洗着尿布,打出层层泡沫。
喻石榴多看了一眼,下意识道:“我看夫郎倒是惯常干活的。”
话说出口,又觉得颇为冒犯。
怎料温野菜抬了抬唇角,接过了话茬。
“姐姐这话说的,可莫要把我当成什么贵人。家里先时是农户,后来靠着我相公的医术,在县城开了个医馆罢了。这回承蒙韦大人赏识,才有来府城的机会。别说洗衣裳了,就是下田种地、上山打猎,都是做惯的。”
话音落下,他顺势反问。
“我听姐姐的口音不像是本地人。”
喻石榴抬起手臂抹了一把溅在额上的水渍。
“夫郎好耳力,奴婢是宛南府人士,早些年家乡遭水灾,逃来了北边。”
温野菜轻叹口气,不由地想到了今年里北地的疫病。
“这天灾人祸,最是让人揪心,姐姐家里人可安好?”
喻石榴摇摇头。
“爹娘死在水灾里了,我带着……带着小弟,跟着村里人往北边逃,后来也失散了。”
在喻石榴说话时,温野菜时不时分神看一眼身边的女子。
他很快察觉到,自己为何觉得喻石榴眼熟了。
因为从这个方向看去,眼前之人,侧颜格外肖似自家夫君。
说一名女子和一名男子长得像,乍听来十分怪异。
但若是拿去和一些个兄妹或是姐弟做比,也就不觉得奇怪了。
他和二妞、三伢,三个人站在一起,向来常常被人说一看就是一家人。
于是,当温野菜听到喻石榴说自己有一个弟弟时,没来由地心头一跳。
他没记错的话,从前那个“喻商枝”,也是逃难来的詹平府,后来沦落为乞儿,被秦老郎中捡回家抚养的。
这个念头升起一瞬,就像是一粒种子,种在了心里。
再往后听喻石榴的一些话,温野菜便觉得对方仿佛也意有所指。
喻石榴说她和小弟是一对龙凤胎,失散那年两人都是八九岁的光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