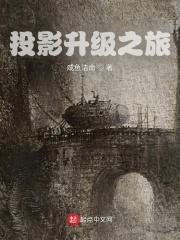52格格党>外室她不干了 > 第 132 章 岁月长五(第1页)
第 132 章 岁月长五(第1页)
岁月长(五)
这别院虽只是个二进的小院子,比不得京中宅院宽敞,但于日益炎热的夏日而言,是个避暑的好去处。
草木丰茂,晚间山风格外清凉。
只可惜经年未有人至,沈夫人当年留下的花死了大半,唯有路旁的野花自顾自地长着,院角那株枝干遒劲的葡萄藤也还郁郁葱葱。
容锦白日走了小半日的山路,最后百级台阶几乎是靠在沈裕身上爬完的,安置下来后一根手指头都不愿动,躺在葡萄架下乘凉。
沈裕端了杯茶水,笑她:“是谁信誓旦旦地说,不必乘车的?”
容锦脸上覆着面团扇,并没动弹,不情不愿地哼了声。
“嗓子都哑了,喝些水润润喉。”
沈裕说着,在一旁坐了,顺势替她揉捏着酸疼的小腿。
容锦这才睁了眼,捧着茶盏慢慢啜饮,余光瞥见篱架上那几道刻痕,好奇道:“这是什么?”
那痕迹显然是谁有意留下的,旁边仿佛还刻了小字,只是夜色之中看不真切。
沈裕循着她的视线看去,手上的动作一顿。
“这是……”尘封已久的回忆被骤然唤醒,沈裕无声地笑了笑,与她解释道,“我少时每年都会随着母亲来此,她总会比划着我的身量,在此刻上一道。”
沈夫人怀他时吃了不少苦,好不容易才生下幼子,视若珍宝,庙中供着的长明灯从没断过。
这一道道刻痕,也是无言的寄托。
容锦闻言,撂开手中的团扇,踩着木屐到了篱架前细细打量。
也得以看清一旁的小字,恰是留下刻痕时沈裕的年纪。
最高的那一道,是十六岁赴边关前留下的。
那时的沈裕身量已经比她要高了,须得稍稍仰头,才能看清那娟秀的字迹。
容锦少时习字,临摹最多的便是沈夫人那两页佛经,透过这熟悉的字迹,甚至能想象出来,她当年是如何担忧却又骄傲地刻下这字,送自己最疼爱的孩子远赴边关。
“锦锦,”沈裕从背后将她抱住怀中,低沉的声音响起,“你还未曾同我提过,自己的事情。”
容锦顺势靠在他肩上,想了会儿:“我娘是个很好很好的人,温柔、善良,只可惜命不好,没能嫁个好人……”
于这世上多数女子而言,嫁人犹如再投胎,至关重要。
却又如浮萍柳絮,身不由己。
自娘亲去后,容锦就对那个所谓的家没有半分眷恋,将容绮接出来后,借着沈裕的势狐假虎威,断了个干干净净。
她不爱与人诉苦,如今再回头看,也无甚可说。
容锦寥寥几句,轻描淡写,低柔的声音仿佛散在了山风之中,虚无缥缈。
沈裕心软得一塌糊涂,不自觉地将人拥得愈紧。
“要喘不过气了,”容锦将被风吹散的额发拢至耳后,轻笑了声,戳了戳沈裕的小臂,“既来了,
我为你再刻上一道吧。()”
说着,便要去寻踏脚的小凳。
不必麻烦。?()_[(()”
沈裕话音刚落,容锦只觉身体一轻,已经被他抱了起来,只一伸手,就能触到葡萄藤垂下的叶子。
不是那种打横抱起,更像是那种抱小孩子似的抱法。
她扶着沈裕的肩稳住身形,脸都红了:“你……”
这回成了沈裕仰头看她,眉梢一抬,眸中亮得似是含了星子,含笑安抚道:“别怕,不会让你摔了的。”
他着常服时缓带轻裘,乍一看像是温润如玉、弱不禁风的书生,但毕竟是武将出身,身形高大,手臂坚实有力。
容锦按着心口,长舒了口气。
抽了发上那支缠枝莲花的发簪,比划了下沈裕的身量,认认真真地在篱架上新刻了一道。
只是发簪终归比不上刻刀锋利,在他怀中也总有不便,刻字时歪歪扭扭,透着些稚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