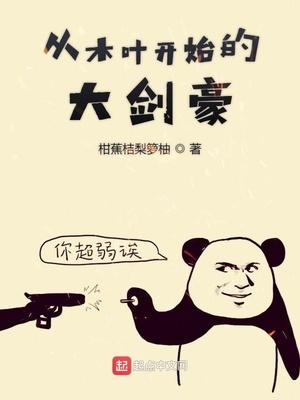52格格党>声声慕我 > 87 慕我(第1页)
87 慕我(第1页)
长廊尽头从侧边连接着住院部的一楼大厅,隔着玻璃的另一面,冷白灯光笼罩在熟悉的身影上,周时慕兀自停住脚步,隐在昏暗的长廊里,复杂视线尽数落在她身上。
三年的时间,不长不短。
从第一次在南大初遇,这三年的时间里,周时慕虽然从未再见过岑声声,但她又似乎一直以特殊的形式一直存在在周时慕的周围。
不管如何讲,云翎的开始都的确是因为岑声声的那些话,创立云翎是周时慕第一次想要完全依靠自己独立做的一件事。
这件事也并非是完全一帆风顺的,他数次处在想要放弃的边缘,又为在想起岑声声那句成为更好的自己再重逢的话而选择坚持下去。
或许人都是输不起的,当一件事情坚持的太久了,沉没成本就越发钉钉高,他也越来越做不到轻易放下。
周时慕甚至都说不清楚,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自己能以一个更好的的身份在未来的某一天与岑声声再重逢这件事,逐渐成了周时慕的一个压在心里的念想。
这三年来,他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有一天能够真正实现。
他不断从别人的口中听说岑声声,渐渐形成一个具象化的她,哪怕从未真正相识过,却又像是早认识了很多年的老朋友。
但周时慕没有预料到,原来真正再次见到她时候,那种预设的重逢情绪抵不过只一眼的冲击。
小姑娘侧过大半个身子背对着长廊这侧的方向,周时慕的视角只能大概看到她的小半张侧脸。她穿一条灰色的休闲长裤,上身罩着件粉色的针织开衫,浓密的长发不再像初见那般扎成精致有技巧的双丸子头,而是被一只皮筋随意松松垮垮地半绑着坠在身后。
周时慕觉得自己那刻生涩笨拙的像个毛头小子一般,久违地感觉到紧张。
隔着透明玻璃在长廊的这侧定住脚步,周时慕很生硬地在设想现在这个场合下如果自己贸然走上前去同她讲其实自己很早之前就见过她,或者直接问她可不可以交个朋友认识一下这种话会有多大的概率会被直接当做是变态。
答案应该也显而易见,对一个不过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来讲,还正碰上亲人住院的大事,此刻一个从未见过的陌生人,在这样的深夜突然出现在自己面前,不用过多纠缠就已经是应该防御的信号了。
周时慕绞尽脑汁,预设
过第一次见面时候的数种场景,却不知道这样直白的场景里,他该以什么合适的身份出现在她面前。
她站着没动,周时慕便就那样静静地观察她。
那个时间,周时慕在犹豫,是不是该仍旧按照原本设想好的借口,先上楼找上周之羡,以云翎新项目试验想找脑科病人合作的借口开始。
她并没有停留太久,在大厅站了不过一分钟,像是终于决定了方向,又开始继续往外走。那刻,周时慕几乎没有任何多余的想法,条件反射地穿过长廊进入大厅跟了上去。
和岑声声之间始终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直到跟着她离开住院部进了对面楼栋的观光大厅。军总附院观光大厅一向是二十四小时开放的,供医院病患家属之类的人过来休息放松,二层的台阶上置一架钢琴,白日里会有退休返聘的老员工过来谈些舒缓的曲子,缓和医院的紧张环境。
晚上的时候,则偶尔会有住院部的家属过来这里摸一摸钢琴,随意弹几下图个新鲜,不过最近早
晚凉,晚上的时候,因为大厅四面敞开通风的缘故,其实很少有人呆在这里。
周时慕看着岑声声进了大厅后一步一步走上二层台阶,最后目标明确地坐在了琴凳上,周时慕在离她大概五六米的距离,同她背对着背,依靠在大厅的一处侧墙里处。
大概猜到她或许也想要弹一曲,周时慕很好奇,她会弹什么曲子。约莫三十秒的时间,他听见一阵熟悉的琴音旋律在空档的大厅里响起。
是首耳熟能详的钢琴曲,《致爱丽丝》。
她的节奏有些缓,听得出来有些生疏,偶有错音,但她没有停,一直在弹。直到,渐渐伴着琴音的,是细碎的一阵啜泣声。
周时慕犹豫着想要上前,移步离开挡住身形的侧墙,转过身时却发现不知何时,琴凳上也不止坐了岑声声一个人。
所以……她是因为身边的男人过来了才哭的吗?那瞬周时慕什么都不确定了。
他冷眼看着靳逸琛抬手,轻抚着岑声声的后背,动作轻柔又亲密。
“别哭了。”琴音突兀断掉,周时慕清楚地听见靳逸琛的声音,他说,“声声,别害怕,有我在,你外婆不会有问题的。"
“我给她安排的可是全国最厉害的脑外科专家,他主刀的手术就没有失败过的,你放心,这次也不会有
问题。"
靳逸琛说的话比不过这刻的亲眼所见,周时慕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这么无力过,他与岑声声,好像只慢了一步,却就慢了所有。
他好像还没有从单方面重逢的喜悦中缓过神,极度欣喜中才刚刚回味过来自己对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女孩子的这种异样情绪应该叫做喜欢。
为着这份喜欢,他所有的准备都才刚刚开始,却猝不及防地被现实当头棒喝。现实残忍地告诉他,对不起,你慢了一步,你来迟了。
这世上没有什么永远等着你的,也许你犹豫了一秒,但是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虽然他们之间隔了三年的距离,然而对周时慕来说,岑声声好像一直在他的世界里,没有走远过。
她更像是一种精神寄托,是周时慕初创云翎的动力,也在云翎搬回京北后,在林哲辉的描述里,他似乎没有错过她的生活。
周时慕厌恶自己这刻偷听别人谈话的自己,很不坦荡。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