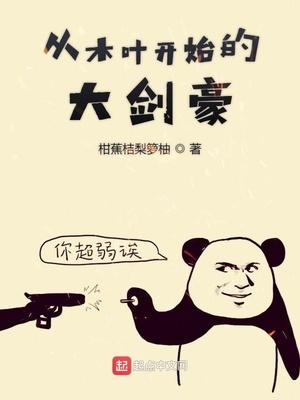52格格党>朕真也想做明君 > 第272章(第1页)
第272章(第1页)
他全然不在乎。
一只手指压住了萧岭的嘴唇。
萧岭抬眼。
谢之容似乎怕极了萧岭说出什么既关怀备至,体面非常,对他们二人都是最佳选择,又令他绝望无比的话了,他近乎于惶然地叫了声,“陛下。”
萧岭停住。
“臣明白陛下的隐忧,臣亦理解陛下的想法,”谢之容继续道,这话他先前想过无数次,说出口本该轻车熟路,此刻却发着颤,“陛下,臣都明白。”
他明白,却又无可奈何。
他想不到有什么办法来消除萧岭对自己的怀疑。
萧岭的怀疑是如此有理有据,平心而论,世间如何寻得萧岭这般的君主?在意识到谢之容有谋反的可能后,萧岭做的所有应对只是不欲再为帝,而非剥夺谢之容的兵权,将他禁锢于方寸之地,或者,干脆以绝后患。
谢之容却宁可萧岭选最决绝无情的方式来解决一切。
“陛下,臣不愿封王,陛下也无需费心给臣任何赏赐。”长睫轻阖,颤抖着,压下的却是晦暗无比的情绪,“臣不想做名臣,臣在乎身后之名,百年之后,史书上说臣是媚上的小人也好,佞臣也罢,臣都不在意。”
不等萧岭回答,他继续道:“臣的所有,皆是陛下所赐,陛下既可予臣,那何妨收回?”
收回您赐予我的声名、我的官位、我的兵权,所有可能助我谋反的一切。
谢之容不知道如何才能让萧岭打消对自己的疑虑,更不知自己要怎样做,才能得到帝王毫无芥蒂的信任。
他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如果他没有资格谋反,如果他和后宫中那些毫无威胁的侍君一样,那么萧岭,会不会就全然相信他了?
矜傲如谢之容,生平第一次产生了这样放在以往,令他觉得不知廉耻,可笑荒唐的想法。
可他不在意。
哪怕以色侍君,他都不在意。
只要萧岭还要他,只要萧岭还喜欢他。
听出了谢之容的言下之意,萧岭此刻的震惊无可言说。
除却震惊,还有心中那如同钝刀割肉般的阵阵痛楚。
他霍地起身,张口欲言,却发现自己喉头苦涩,“含章,你……”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如最温润又最高不可攀的玉,入最剔透又最寒凉无比的冰,便是困顿折翼,也不曾生出任何自暴自弃认命之心,矜高傲慢,野心勃勃的男主。
情之一字竟能至此,能湮灭于无上权力的欲望?能生生磨断,不可攀折的傲骨?
此刻跪在他面前,说,臣什么都不要。
谢之容望向萧岭的眸光无比清醒。
谢之容当然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当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直起腰身,随意地打开那匣子。
内里放着的,并非书信,亦并非何种稀世珍宝。
那是一副束具。
谢之容在萧岭的注视下自然地撩开束起的长发,将束具,扣在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