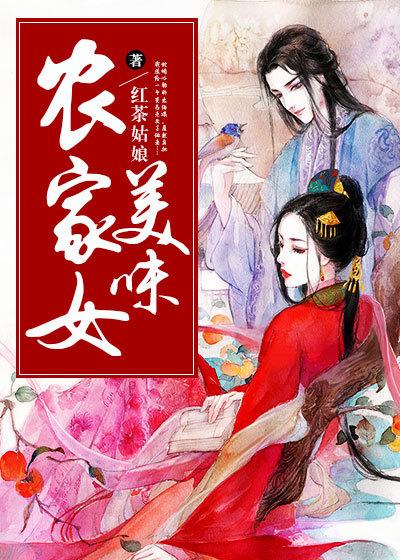52格格党>温香艳玉 > 第101章 番外二 宵宴上(第2页)
第101章 番外二 宵宴上(第2页)
温宴端着刚熬好的粥进来,风风火火地招呼他:“把粥吃了,你先前睡着了,我给你身上伤口处换了买来的止血草药,我还熬了内服的药,那药铺的掌柜教我的,一会儿你吃完粥再喝那个。”
凌祈宵默不作声地将粥接过去,这粥比早上那碗要丰盛得多,加了不少这人从镇里买来的好料,他自己也盛了一碗,狼吞虎咽几乎要将舌头都给吞下去。
吃饱之后,温宴一抹嘴,抬头问他:“你傻看着我做什么,赶紧趁热吃啊,你总不会要我喂你吧,你手又没受伤。”
凌祈宵点点头,很快将粥给喝了。
温宴笑了笑,去给他端药过来,还打了热水,让他稍稍梳洗一二。
“喂,你是碰上了仇人吗?为何会受了这么重的伤?”
凌祈宵却问他:“你叫何名?”
温宴一噎,道:“温宴,我叫温宴。”
“哪个宴?”
温宴随手捡起根木棍子,在地上写字给他看:“盛宴的宴。”
凌祈宵轻眯起眼:“你识字?”
“认得啊,我认得的字可多,”温宴得意解释,“我爹想要我念书考科举,五岁就将我送去村里赵老先生家里开蒙,我这名字也是他给我起的,我被逼着念了几年书,字都认得,文章也念过不少嘿,可我实在讨厌念书,不乐意学,宁愿跟着我爹打猎,后头我爹就随我了。”
“那你爹人呢?怎未看到他?”
温宴嘴角的笑滞了一瞬,又嘟哝道:“娘跑了,爹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
凌祈宵闻言皱眉:“你几岁了?”
“十五,我本来打算去投军的,说不定以后还能当个大将军,但我叔他们不让,说我一个人去外头会被人欺负,说什么都不肯,我打算再过两年,等我十七了,就偷偷溜出去。”
温宴大咧咧地说着,大约是一个人在这山里住久了,第一回碰到能说话的人,即便这个书生总是一副冷冰冰的棺材脸,看着不好惹,他跟他说话还挺高兴。
他的笑脸格外晃人眼,凌祈宵移开目光,没再多言。
温宴看他一眼,好奇道:“你呢?你真的碰上仇家追杀啊?不能说吗?”
半晌,他见到那人的神色阴下,微颔首:“嗯。”
温宴一阵唏嘘:“那你这仇家可真可怕,那么大一个血窟窿,是剑伤吧?”
“你连这都觉得可怕,还想去投军?”
温宴:“……”
这人怎么这样?
入夜,温宴把他今日新买的被子抱来给凌祈宵,顺便抱起自己原本那床:“你睡这里吧。”
凌祈宵看着他:“你睡哪?”
“我爹的屋子空着的,我去收拾一下,能住。”
凌祈宵的目光落到他手中被子上:“脏了,你用新的。”
“不用啦,你这种富家公子哥,肯定睡不惯别人的被窝,你睡新的吧。”温宴大方地摆摆手,反正这人给了他那么多钱,他一点不委屈。
目送着温宴出去,再从残破的窗纸缝隙间看到他走进对门的屋子,凌祈宵盯着那一处看了许久,直到那间屋中的油灯熄灭,他又在黑暗中坐了一会儿,重新躺下。
阖上眼,挡去了眸中晦暗。
温宴拉下床帐,又悄悄把带上床来的油灯点燃,趴在被褥上,将凌祈宵给他的钱袋中剩余的碎金碎银都倒出来,算了一遍又一遍,再拾起那碎金子,用牙齿咬了一口,咬得动,果真是真的。
他眉开眼笑,想将之与自己之前存的银子搁一起,这才想起来那人还睡在他屋子里呢,他的银子就藏在枕头下……
算了算了,温宴努力安慰自己,那人这般有钱,出手就是一袋钱,肯定不会贪他五两银子的。
这般想着,他放松下来,将那些金银小心翼翼地重新装回钱袋里,抱进怀中,贴在心口处,这才缩进被窝里,闻到了上头另一个人身上的味道,不自在地吸了吸鼻子,很快睡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