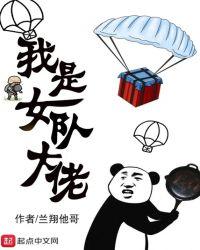52格格党>绿茶靠套路被肥啾少爷投喂后 > 第243章(第1页)
第243章(第1页)
温柔熟悉的声音并不算很清晰,却在入耳的瞬间就驱散了所有的焦虑不安,莫岁的眼中倏然亮起盈盈的光晕。
莫岁还有点懵,他无意识地一阵点头,直到听到褚洄之第二次叫他的名字,他才恍然惊觉褚洄之此刻看不到自己。
“在,我在。”
他赶紧回答,发出的声音却吓了他自己一跳,紧绷得不像话,差点破音,简直没法听。
褚洄之显然也听出了莫岁声音的异常,他问莫岁:
“是不是打扰你休息了?把你吵醒了?”
“抱歉,实在找不到更好的机会了。这里看不到时间,我也是估算现在应该不算特别晚,但好像算得不太准?”
“没有。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二十三分五十二秒。”
莫岁完全没在思考,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
“本来也没睡着,正在想你。”
这一记直球打得太过突然,说话人和听话人都没想到这一茬,术阵两端同时传来呼吸微微停滞的声音,心跳声随后猖狂地占据胸腔。
片刻后,褚洄之愉悦的低笑声打破了暧昧的沉默。
莫岁脸上有些发烧,他翻身趴下,把脸埋进了蓬松的靠枕。
“笑什么。”
声音被闷在柔软的填充物里,其中羞恼的成分却依旧非常鲜明,莫岁离被彻底惹毛就差一点点。
“本来就是在想你,这几天一直在想你,有什么好笑的。”
莫岁没有抬头,攥着暖玉的手却诚实地将此刻充当听筒的玉牌紧紧贴到了耳边。
也因此,他清晰地捕捉到褚洄之声音深处的喑哑,那是过度疲惫损耗的身体无论如何也没法自行遮掩的。
褚洄之微笑着对他说:
“没有笑你,岁岁。听到你的声音是我这几天最幸运的好消息,怎么办,实在没法不笑。”
这句话几乎是在明着说褚洄之这些天过得非常辛苦。
一个习惯避重就轻不让他担心的人能说出这种话,无疑意味着背后还有更多被隐瞒的艰难。莫岁原本晕乎乎飘在云端的心脏猛地往下一坠,整个人像被泼了一盆冷水。
“……可以让我看到你吗?我很想见你。”
莫岁没忍住,小声地提出了任性的要求。但理智很快占据上风,他摇头,否定自己刚才说过的话:
“算了,当我没说。这肯定很难。”
“你口头回答我就行,你说,我都信。”
莫岁深呼吸着平复了下心情,开始认真地一句句询问其实本没有必要询问的无聊问题:
“你这几天吃的什么?”
“睡得好吗?”
“有没有受伤?”
“有没有想我?”
不管莫岁提出的要求是否无理,在褚洄之这里,都只分两种回应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