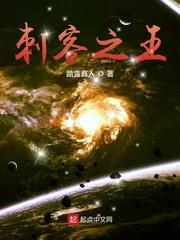52格格党>银灯映玉人 > 第 69 章(第2页)
第 69 章(第2页)
字刻得差不多时,该抽针了,熹色对着落下最后一缕的滴漏,算准时辰,起身,为李朝琰将银针都取下来。
之前侍医来过一次,告知她可以用针灸行以辅助治疗时,熹色想,她日日都在李朝琰的身边,用针刺来疗愈血瘀之伤,是再方便不过的。
未几,侍医又来了。
但这个侍医,与之前熹色见过的罗适中,根本不是一个长相。
等他为陛下看诊,重新换了浸泡药汁的绸带之后,便留下了方子退下了。
熹色捧起绸带绕到李朝琰的身后,替他系上。
“郎君,那个侍医,好像不是之前那个罗侍医了。”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了,她想不起罗适中的面貌,因此也不是十分肯定。
李朝琰挼搓着掌心的刻刀柄,点了下头:“罗适中是太后的人。我的毒,正是他下的。”
闻言,熹色的指尖缩了一下,她垂下眼眸,震惊地看着一脸平和的李朝琰。
对于接受自己瞎了这件事,李朝琰比大部分人都更冷静。
尽管他失明的缘由,比绝大多数人都更心碎。
熹色的心被触动着,仿佛湖畔垂落的柳枝,长长地,抵到了水面,点开一圈圈拂向堤岸的涟漪。
将他的绸带绑好以后,熹色从身后,抱住了李朝琰。藕臂垂落交叠在他的胸前,那是一个带有抚慰意味的拥抱。
熹色把下巴抵在李朝琰的发丝之间,从他堆叠的墨发间,释出淡淡的芙蕖清香,但比夏日荷塘之中的那股花香,又独添了一丝幽冷。
李朝琰再一次感到,若能一直伴她左右,终生不复光明,也是他该为此而付的代价。
更何况,有她在,已是他最大的明路。
笃笃笃。静寂之中,有人敲响了门扉。
李朝琰在疏影居养病,知道的人极少,就连庞墨儿,都因为天子要以假乱真,演他此刻身在行宫,而到行宫去侍奉并不存在的君王去了。
来疏影居的人,除了侍女和侍医,便几乎再无其他人。
熹色茫然着松开了手,缓缓挺直脊背,朝外望去。
夜色全暗,一门闭户,不见来人。
李朝琰的唇角往上扬了一点弧度:“去和他说说话吧。我这里无事。”
熹色不知道那人是谁,好奇地寻了过去,拉开门,只见夜雾之中,长身立着一个少年。
少年虽然面貌仍显稚气,才不过十来岁,但已经出落得身量极高,几乎不逊于李朝琰,比熹色还要高半个头,她须得仰起脑袋,才能和对方碰上视线。
那个少年身着湖蓝软缎裁成的圆领及膝袍,足蹬黑靴,外罩不知材质的裘衣,长眉似漆,双眸如星,薄唇天然带一抹粉红,不用描画,便显得很精神,很好看。
只是,瞧着有一分说不上来的眼熟。
或许是错觉吧。
熹色瞧见他,手中端着一块托盘,上面有毛巾、香膏,还有一些药材磨成的粉,用瓷罐盛着。
黑夜中廊下的灯笼照着,一缕风卷了一丝雪落在他的眉毛上,化成了细细水迹。
熹色怔愣一瞬,忙侧身让开。
“你是服侍郎君沐浴的么?”
她在看那个少年,而少年也在看她。
听到她问,少年缓缓颔首:“是的。”
熹色不知为何,觉得他看着很是亲近,微微地笑了一下:“陛下沐浴不喜欢女侍近身,有劳你了。”
不光不喜欢女侍近身,连她,都会让李朝琰感到不自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