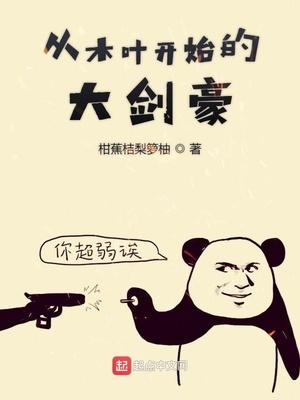52格格党>骄婿 > 第232章(第1页)
第232章(第1页)
他后半句话是在讽骂伊邪,萧真回了一声口哨,伊邪怒极悲极,大喝一声,挥刀便横砍向萧澜!萧澜仰身堪堪躲过,剑尖斜刺,划向伊邪的双眼。殿中人声悄然,只剩刀剑相撞的铮鸣声。打了几十余招,最紧张的并不是萧澜自己,而是萧真和常叙。已经到这一步,万不敢叫圣上出什么岔子,又不敢立即去帮手,尤其萧真,他心里头知道,当日皇后也被掳在汉中,萧澜心中必然是有口气,这会儿之所以要跟伊邪打,为的就是亲手给皇后报这个仇。可伊邪单论功夫,当真不差。萧澜想要取他性命,并不容易,兴许得受伤。像是要印证他的话,萧澜打法变了,全是拼着自己受伤也要攻伊邪要害的狠招,伊邪大声骂了句匈奴话,一刀扫在萧澜下盘,萧澜甲胄崩裂,腿上挨了一下,却面不改色,身子前扑,伊邪刀往上带,横切他的腹部,萧真与常叙一急,边往上冲边喊:“皇上!”就在萧真的剑将将刺到伊邪之迹,萧澜将天子剑送进了伊邪心口。四目而视。须臾,伊邪萎到在地。门外响起几声猛烈的撞门声,随即被拉住,一个尖利的声音在外面喊:“别杀他!萧澜你别杀他!留他一命,听到没有?萧澜!”伊邪的眼神亮了一瞬,有点儿复杂的看着萧澜。萧澜知道是谁,充耳不闻,剑柄毫不迟疑地用力一绞。匈奴年轻的新王毙于剑下。他先是皇上,而后才是萧澜。殿中静了片刻,门外的声音尤在,萧澜闭了闭眼,往外走。秦宛一身农妇的粗布衣裳,正被被几个人拽着,要往外扔,殿门一开,萧澜瞥了一眼,什么也没说。萧真示意把人放开,秦宛跑到殿内,半晌,疯了一样跑出来,一头便要往萧澜身上撞,被人拦下,她满脸是泪,破着嗓子喊:“萧澜!你到底要怎样?要怎样!”萧澜背着身子,脑中有霎时的空白,萧真蹙眉看了看秦宛,过去吩咐:“先关起来。”常叙忙着喊御医来包扎伤口,萧澜一语不发,几下扯开甲胄,一手探进怀里,摸到延湄的信尚且好好的贴在怀里,这才徐徐舒了口气,提精神道:“包好些,多上些药,尽量在回宫时能瞧不出来。”回京十一月底,大军班师回朝。已经临近腊月门儿,又打了大胜仗,全军上下俱透着股子喜庆劲儿。路过的几个州、郡全都扫街清巷,盼着能够一仰天恩,然而当今陛下实在是很着急回家,只在汝阴和钟离郡各停留了两日,其余地方都是一走而过。腊月十二,王师进了南方地界,气候不再如东边那般干冷,却也寒浸浸、凉嗖嗖,秦宛拢着披风往外看一眼,冷声道:“你们皇上呢?我要见他。”——这已经是她一路上不知第多少回说这个话了。马车两旁的禁军目视前方,只当没听见。“听到没有?!”秦宛见他们没有反应,陡生怒意,一手扶着车门,站到车辕上,作势要跳,“还不去通禀!”随车的禁军见她就要撒手,顿了顿,只得先去禀韩林。没多会儿,韩林打马过来,看了一眼,今日风大,吹得秦宛身子往后仰,七皇子探出半个身子,两手抓着秦宛的衣裳,叫她:“会、会掉下去,母亲快、快回来。”韩林蹙眉:“夫人还是仔细些,自己掉下车不要紧,身后还有孩子。”“去跟你们皇上说”,秦宛拽了一把七皇子,咬牙:“他不见我,我便带着他的七弟一块儿跳。”韩林嗤笑一声,打马走了。大军仍在行进,并没有因她的话而降下速度。韩林走了半天前面也没动静,秦宛冷笑一声,回身使劲儿一扯七皇子的手,攒着劲儿当真从车辕上跳了下去。然而,她那一下并没能完全扯开七皇子的手,七皇子抓得死,冷不防被她一拖,也随着摔到了马车下。周围乱了一阵子。大军正在赶路,行进速度不慢,而且这个时候他们正在野外,秦宛一摔下去就感觉到一阵钝痛,滚了几滚,不知被什么踩了胳膊,,眼前一黑,在扬尘里闭上了眼睛。……再睁眼时,她先皱眉抽了口气——左胳膊包扎着,疼得厉害。抬头,她看见了逆光坐着,离她三尺开外的萧澜。秦宛也顾不上疼了,噙着嘴角刻薄道:“怎么,大梁陛下终于肯见我这个匈奴的俘虏了?”“你是汉人。”萧澜脸色有些冷,声音也听不出情绪。“哦,是啊”,秦宛漫不经心地挑挑眉,四下里扫一眼,他们似乎是临时到了一间农舍里,屋中陈设简单,一榻一桌,萧澜坐在桌边,房门敞着,萧真和韩林不避及地就守在门口,秦宛笑了,口中愈发尖酸:“我是汉人,我怎么都快忘了?对,不能忘,我还服侍过你们先帝的。那陛下此时总算愿意见我,是不是也需要秦宛的服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