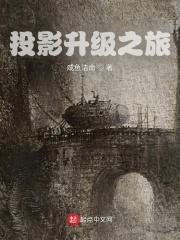52格格党>我和我的母亲(寄印传奇) > 第72章(第1页)
第72章(第1页)
陈建军的喉结顶在我的虎口,接连滚动了好几下,每次都发出一种咕噜噜的声音,像是牛在反刍。
他的脸好红啊,腮帮子似乎都鼓了起来,无框眼镜挂在鼻梁上——我以为它会在头部的剧烈摆动中掉落,但事实上并没有。
这大概是我离陈书记最近的一次,近到眼前的这张脸跟记忆中的那个白面书生有些对不上号,比如平头上隔三岔五冒尖的白头发,比如右侧鼻孔里悄然探出的鼻毛,比如左耳下小指肚大小的青色胎记,再比如有些发黑的嘴唇、堂而皇之冒出的火疖子和眼角、额头处藤蔓般密布的褶子。
但法令纹一如既往,甚至,它们在肌肉的痉挛中波动起来,消失复出现,变浅又加深,宛若这个初夏傍晚的一道光。
这让我心里一阵麻痒,手便不受控制地加大了力度,一种幽幽的清香从车窗飘来,充斥着鼻腔,我也说不好它到底来自哪里。
几乎是点着烟的一刹那,我就朝那辆奥迪A6冲去,副驾驶位看不清楚,但长发披肩,显然是个女人。
夕阳戳在哨亭的琉璃瓦上,使后者跳跃着,似要淌出血来。
身后是五花八门的大音量节拍,旋律欢快,却震得我头皮酥麻。
确实是陈建军。
喘气般,我猛吸一口烟,踉跄着绕过车头。
奥迪有些措手不及,只能急刹车,可以想象,陈建军难免气急败坏,他骂了一句,之后索性摇下牟窗,探出头来。
这厮大概还想说点什么,但看到拽住车门的我时,立马没了言语。
我同样目瞪口呆,除了鼻子出气,再无动静。
副驾驶位的女人嘀咕了一声,又凑过脸来问咋了——当然不是母亲,而是那个细眉细眼的葛家庄女人。
得有好几秒,陈建军轻咳了一下,扭过脸又迅速扭了回来,手搭在车窗上没动。
我条件反射地吸了口烟,松开拽着车门的手,犹豫着是否该就此离去。
但周丽云叫住了我,“咋回事儿嘛?”
她提高嗓门,短暂的停顿,“哎——是你呀,那个那个……”
她并没有“那个”出什么来,但我还是害臊地打了个喷嚏。
是的,害臊得厉害,于是鼻涕、烟灰和满头大汗簌簌落下。
那支吸了半截的红梅射往车门,又弹到了地上。
陈建军明显躲开了他的猪脑袋,好一会儿,在我妄图再打两个喷嚏而未果后,他扶扶眼镜,张张嘴,但依旧什么也没说。
周丽云却有些喋喋不休,我听不出她是高兴、抱怨还是疑惑,我甚至听不清她在说些什么。
陈建军摆摆手,笑了笑——可能是吧,至少那对法令纹又浮现出来,“完了完了,”他说,“以后小心点儿。”
只觉脑子里嗡地一声,我抹了把汗,然后就卡住了陈建军的脖子。
他只来得及哼一声。
那颗猪脑袋抵在靠背上,在摆动中咯吱咯吱响——当然,是车座在响。
陈建军很快来掰我的手,先是手腕,再是大拇指,力度不小,以至于我险些把另一只手也伸过去。
他想说点什么,却只是露出了参差不齐的牙,被奶奶夸赞过的那双大眼里满是血丝,我觉得这货有黄疸也说不定。
大概有一个世纪那么久,周丽云开始拍打,喊叫,她挠我的手,说:“你疯了!疯了!”
“来人啊,来人啊!”
她冲车窗外喊。
眼镜总算滑了下来。
陈建军把车踢得咚咚响。
夕阳还残留着最后一丝光晕,空气里弥漫着一股说不出的香甜,让人忍不住想打喷嚏。
病猪的脖子汗津津的,越来越滑,仿佛两栖动物褪去了一层皮。
周丽云挤过来,似是要咬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