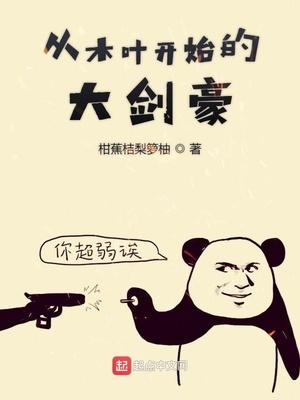52格格党>师姐说,要善良 > 第52章(第1页)
第52章(第1页)
甚至没有亲口对他说上一声再见。从岛上出发去无量山,最多不过半个月,一年的时间,就算走着去也早就到了。可自那天谢慈离开后,他既没有出门,也不曾派人去打听,甚至刻意地不去关注外界的消息。江湖上的事,早就与他无关,若非为了给裴升送白风原的地图,他不会让水玲珑有机可乘。披衣下床,整个人已是没了睡意。这间扶摇殿的屋子能望到海面,深夜里,海与天之间唯有不甚清晰的分割线,是近乎漆黑的墨蓝色,他听着海浪风声,于黑沉沉的夜幕中,遥遥望见了逐渐明显的火光。谁来了?他既睡不着,索性一个人出了房门,沿着山道往下走,待得他人到了海边,那艘大船也近在眼前。望着大船,萧无忌神情不明,心内已轻轻叹了声。船上有官兵拿着火把,有人让出一条道,在无人喧哗的寂静中,一个身着凤纹红袍,头戴金冠的俊秀青年人率先走了出来。这名青年不过二十出头,算得上丰神俊秀,他面上不带什么表情,只是走动之间,眉目间隐约闪过一抹忧心之色,似心中藏着什么大事般。萧无忌蓦然出声,“十七。”他的声音沉静肃然,自风声和涛声间穿过。那青年听见声响,抬头望见不远处负手而立的白衣人,当即是面上一喜,“皇兄!”当今齐国十七皇子萧越,已在入秋前被册封为太子。册立太子不久,齐国皇帝萧武因病驾崩,随后太子继位,正式成为齐国新君。新君上台,本为多事之秋,齐国皇室占了北朝半壁江山,却因凉城之战连输昆厥十五城,自此国力不济的形象深入人心,好容易在雍州打了一场胜仗,昆厥人总算安分了一段时间。然而自先帝逝世,国中震荡,萧越上台后,不过短短半月,就在宫中遭遇了两波刺客。如今冒险来到东海,不过是为了请他这个“三哥”助自己一臂之力。萧无忌昔年闯荡江湖,被人称为“逍遥侯”,赞他修为出众,人品洒脱,为当世第一豪侠。却甚少有几个人知道,萧无忌乃北朝文帝之子,若非“照元宫变”,文帝被叛将梅璟所杀,一场大火卷入禁宫,“三皇子”也许亦成了刀下亡魂。旧事早已从萧无忌心间抹去,他望着这位“弟弟”,似乎已预料到了他的来意。“皇兄,上次一别,你我已经十年没见,我都不知道你去了哪里,多亏了东方先生指点,我今日才能见你一面。”萧越和萧无忌自然不是亲生兄弟,只不过兰皇后的胞妹亦是当今太后,萧无忌虽未与他相认,可为护这位表弟,不惜将自己的结拜兄弟裴升“送”给了他。裴升原是江湖侠客,却有兵家之才,他荐他为将,这些年,大齐未丧在昆厥铁蹄下,有他一半功劳。而萧无忌为了避嫌,亦不再以“逍遥侯”的名号行走江湖,他的逍遥剑法练到炉火纯青,唯一的念头就是将此功传续下去。虽说自封为掌门,可他迟迟没有真的广收弟子,除了这片海域,江湖上并没有几人知道这是萧无忌的地盘。认真算来,他唯一想收的弟子大概就是谢慈。想到这个人,他蓦然心内空荡荡的,仿佛被谁挖走了一块。萧越见萧无忌神情不悦,猜测大约是自己来得唐突,忙道,“皇兄,我来不是为了别的,只是我很久没见你了,母后也听说了你在东海,说……我可以来见你一面。”他说的情真意切,态度亦平易近人,萧无忌的脸色却更是肃然,眼睛里没有一丝笑意,他直视着面前衣冠非凡的青年,蓦然俯身拜下,声音在夜风中显得平静漠然。“陛下,此地风大,还是去屋内一叙吧。”萧越俊秀的脸上略微僵硬了一下,仿佛没料到昔年的三哥变得这般生疏。宫内带来的卫士欲护送他进去,望着前方带路的身影,刚刚荣升为新君的太子却不喜欢这番架势,只道,“皇兄,等等我!”护卫们还想追上去,一人却蓦然出声,“让皇上去吧,如果天底下只有一个人不会害皇上,那便是萧掌门了。”说话人是个约摸三十出头的男子,生得清俊无双,目光湛然,一双瑞凤眼炯炯有神,正是名扬天下的东方先生。护卫们只得作罢,眼睁睁看着皇帝离去。“陛下,请坐。”萧无忌沏了茶,将之送到桌边,茶水清澈见底,几片绿叶漂浮其上。年轻的皇帝愣了一下,逍遥山为这片海域中面积最广,地势最复杂的岛屿,山上的建筑,除了火蛇殿,皆是古朴雅致,高低起伏的木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