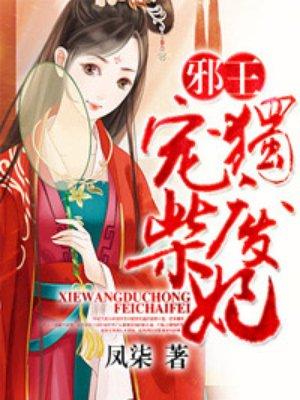52格格党>陛下究竟怀了谁的崽 > 3040(第28页)
3040(第28页)
严瑞几乎要痛哭流涕了,不停磕头道:“八月十二圣上策御马猎鹿,不承想却被鹿冲撞,跌落马背……小人、小人实在是不知道了,大人明鉴呐!小人该说的都说了,大人饶了小人吧!”
顷刻之间,霍洄霄脑中有什么东西“轰”地一下炸开,他掀开帘帐,大步朝外走去,将牙斯的惊呼抛之脑后——
“公子?!”
天穹一弯清冷的月,朔风刮骨,飞电从远处奔驰而来,霍洄霄飞身上马,扬鞭直冲……
原来……原来那一夜沈弱流并非自愿,而是被下药的!
怪不得那夜沈弱流会莫名其妙出现在他帐子里。
……怪不得沈弱流不愿意提起那夜之事。
他竟然在沈弱流被下毒的情况下对他做出那等事……那样倔强,那样矜贵的人,竟然被他乘人之危,压于身下百般磋磨。
当时的他定然是觉此事屈辱肮脏,亦觉他肮脏不堪。
一点落在白纸上的污秽。
……怪不得他对自己那般冷漠,怪不得他逃了。
沈弱流有洁癖,他怎么能接受这样污秽不堪的事。
他怎么能直面乘人之危对他做出此等肮脏之事的自己。
万般表现,都只因那一夜并非沈弱流自愿,而是被迫。
于他而言,那一夜就是个肮脏的错误。
此刻真相大白,浑身血液涌现头顶,霍洄霄额上青筋暴起,霍洄霄几乎要疯了。
他的爱恨,他的愤懑,怨怼,自以为的缱绻纠葛就如同一个笑话一般被摊在青天白日之下。
那些对于沈弱流的针锋相对,此刻再看就像是一拳头打在棉花上,令人无力;就像是一个跳梁小丑唱着独角戏,令人发笑。
天穹黑沉沉的,月光犹如幽冷的霜,远处山林传来阵阵狼嗥,飞电疾驰不知道去往何处。
这个真相显然不是他想要的,霍洄霄心中犹如关了一只发狂的野兽,混乱疯狂,想即刻骑马飞驰去见沈弱流。
可见了他该说什么?
说我乘人之危睡了你?说我那时候不知道,对不起?
又该问什么?
问那夜之事,要杀要剐,他为何不与自己直接挑明,而是装作没事人一般对自己的一切试探,戏弄,针锋相对无动于衷?
沈弱流绝不会坦言。
……飞电疾驰,霍洄霄陡然松开马缰身子仰面翻倒于地,巨大的疼痛使他混乱的心得以片刻宁静。
爱不成爱,恨不成恨,说不得问不得,动不得……不知该向谁发这股鬼火,不知该向谁去讨这笔债。
朔风呜咽,如泣如诉,霍洄霄抬起手背盖住双眼,过了许久,他唇角勾起一丝冷笑,起身上马朝郢都飞驰而去。
……他是对不住沈弱流,可沈弱流亦有对不住他!
*
沈弱流在小黄门的服侍下换了件干净衣衫,又用清水将脸侧那混账东西揉上去的药汁擦干净了,蹙眉左嗅右嗅却仍旧觉得身上还是有股子药味。
窗边,福元正忙忙碌碌指挥着侍女将榻上东西都换了干净的,看沈弱流从屏风后出来,一下呲溜过去,
“哎哟圣上,您可注意脚下,别踩着碎碗片扎了脚,奴婢扶着您去那边先坐着。”
那碗被霍洄霄撞下来摔了个稀碎,瓷片满地都是,几个小黄门正在弯腰收拾着。
沈弱流想起霍洄霄便觉气不打一处来,骂道:
“那个混账东西!喂不熟的疯狗!朕遇到他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了!亏朕先前竟还想着与他平和相处,现下看来简直是可笑至极!”
福元也觉得世子爷屡次犯上,实在是太过放肆,不过这回倒也算做了件好事……他扫了眼地上的碎瓷片,笑道:
“圣上息怒,别气坏了龙体,方才您没进多少东西,奴婢去司膳房拿碗甜羹来您吃了垫垫?”
沈弱流这些日子恶心的毛病好了些,肚子里揣着个小混账,饿得倒是比以往快了,这会儿胃里正叫嚣着,气也随之消下去,点了点头,
“说起来朕也有些饿了,你去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