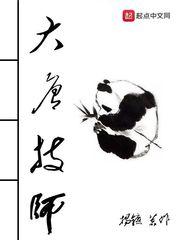52格格党>不悔 > Chapter 14(第1页)
Chapter 14(第1页)
他们的关系就这样定下了。
尽管这和他想象中的恋爱并不同,但他管不了那么多。
那天他带她一起离开的时候,所有人看他的目光都透着复杂,大概觉得世界上最不可能在一起的两个人在一起了。
他推着轮椅带她走,她扭头轻笑:“他们大概觉得你疯了。”
他这样的人,找什么样的女朋友都不难,没必要在她这里冒险。
“那你觉得呢?”他问。
他只关心她的想法。
“我觉得你晚上可以来我家。”她语气轻缓,意味难明。
他有很多话想说,但最后只说出一句:“好。”
到最后他也不知道那天她因为什么而露出那种悲伤的神情。
她像是一团镜中花水中月,无论映照得多么清晰,多么栩栩如生,始终隔着什么,触摸不到。
他早该知道,他们从来没有真正靠近过。
只是即便只是一层裹着毒药的糖霜,也足够甜,足够诱人了。
怪他自己,怪不到任何人。
“腿怎么受伤了?”那晚他去她家里的时候,只问过她这个。
唐不悔笑说:“我说被人打的,你信吗?”
“谁?”他语气严肃。
她便笑了:“逗你的。”
“那到底是怎么伤的。”他依旧固执问。
她回答了吗?好像没有,他们接吻了,唇齿纠缠,呼吸交错,她接吻的时候眼神很专注,情意绵绵,好像眼里只有他。
那眼神里有浓烈的情绪,恍惚让人觉得,她真的是爱他的,真的情深难抑,不可自拔。
季闻识觉得自己内心仿佛有一个无底的黑洞,在无限地吞噬着他的情绪。
她的房间里依旧是繁杂富丽的样子,夜里灯开着,流光溢彩,仿佛置身在中东宫殿,浮夸又俗气,却因她的存在添了几分贵气。
她去洗澡,衣服随意丢在沙发上,他就坐在她房间里回复邮件,偶然一抬头,看到墙壁上挂着一件不属于这个房间的东西,格格不入,以至于吸引他目光。
那是一副画,素净淡雅,勾勒一个女人的肖像,但脸却是模糊的,于是他走近了,仔细看,但站得近,连模糊的轮廓都看不到了,只能看到一团意味不明的色团。
这才发现,画面很清雅,但却很压抑。
唐不悔从浴室出来,走得缓慢,看到他在看那副画,露出复杂的神情,像是想起了什么,又像是在厌恶着什么。
然后突然问一句:“你信命吗?”
季闻识幼时过得并不容易,那是母亲和父亲冷战最盛的时期,甚至彼此都不愿看到对方,但因为种种利益纠葛,却不得不纠缠在一起,甚至他们都无法在家里好好说上两句话,更别提同床共枕。
他父亲对他态度的极端冷漠,让他母亲彻底爆发,这场无爱的婚姻里,她生下了一个不被期待的孩子,她一边爱他又一边痛苦,因为丈夫的冷漠而感到更深刻复杂的痛。
于是她找借口将他暂时寄养在自己母亲那里。
老太太那时并不认同,但不忍一个婴孩被迫卷入到父母的战争里,最后还是把他接到家里住。
季母那时是在预备随时离婚带儿子独自生活的。季家并非野蛮豪绅,以季父对儿子的态度,和本身的脾性,从他那里获得抚养权并不难。他虽然是个十足凉薄的人,但却并不是个恶人。他只是不爱她罢了。
幼时的季闻识便很少话,早熟、过分理智,刚会走的年纪就已经懂得大人之间的种种龌龊龃龉,但他也不能做什么,就那么安静地长大了。
外婆和荣姨把他教得很好,温和、守礼,身上有季家长辈喜欢的儒雅书卷气,他开始偶尔回季家,随着父亲母亲和爷爷出席一些必要场合,到了十几岁,就彻底回家去住了。
在同龄人中,他的出类拔萃已经到了有目共睹的地步,老爷子亲自教养他,给他请最好的老师,带他出席一些本不该他去的场合,把他当做继承人培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