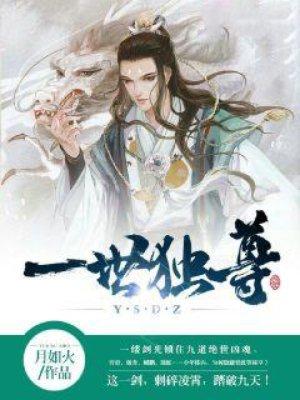52格格党>蛇行春江[刑侦] > 第55章(第2页)
第55章(第2页)
来回跑了几趟,他晕头转向,猛地向前栽倒,被人扶住了。
“先生!先生你怎麽样?”
“江南区公安分局,麻烦快点儿。”
斯文坐在副驾,想了想,把双肩包放到地上。
包很旧了,拉链拉不拢,里头是香烛、纸钱。
斯文不懂做法事的规矩,反正所有要求一概应下,包里还塞了童男童女,彩纸糊在竹篾上,大白天挺吓人。
司机瞟了眼,“上海来出差啊?”
斯文的目光停了两秒,“什麽?”
“你不是上海财经的吗?”
司机指背包上模糊的徽章,“我侄儿也有这个。”
斯文扳过来一看,上海财经建校九十五周年经济学院校友联谊会。
他马上戴上耳机拨电话。
“叔叔我问您个事儿,这个包是金大昌的吗?”
一边查上财九十五周年校庆,是2012年。
“哪年给您的?2010年?不可能,您再想想。”
最后还是卫蔚妈妈接起来,哭多了声音沙哑。
“不是2012就是2013年,我生日是端午节,岳梅包粽子好吃,特意送过来一趟,包忘了拿走,后来我找她几遍,她推来推去的,就算了。”
“你们不是前后楼住着麽?”
“宿舍拆了就散了,她搬的远。”
斯文问,“她搬哪儿去了?”
卫蔚妈妈说了个地址。
斯文默念两遍,问师傅,“您知道麽?”
华南医药在斯文印象中,是家规模庞大技术领先的上市公司。
没想到当年起家的厂房,就龟缩在城市边缘,城乡结合部的山坳里,门口集团公司的牌匾十分威风,但绕到山路往下俯视,就会发现厂房停産多年,仓库半边墙都垮了。
“阿姨,您说金大昌在仓库做保安?”
“做保安好,管吃管住,岳梅也有个地方待着,她又喜欢种花。”
可怎麽看,这儿都不像是有人种花的样子。
斯文回到大门口亮警官证,大拇指摁住‘实习’两字,虚晃一枪。
没想到老头儿眼睛挺尖,边开门边笑,“刚毕业呀?”
“你找谁?”
斯文不说话,先把他打量又打量。
老头儿干瘦,年龄对得上,笑呵呵的,但皮肤白,右边颧骨上一大片显眼的胎记,肯定不是金大昌。
“师傅,您在这儿干几年了?”
“十来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