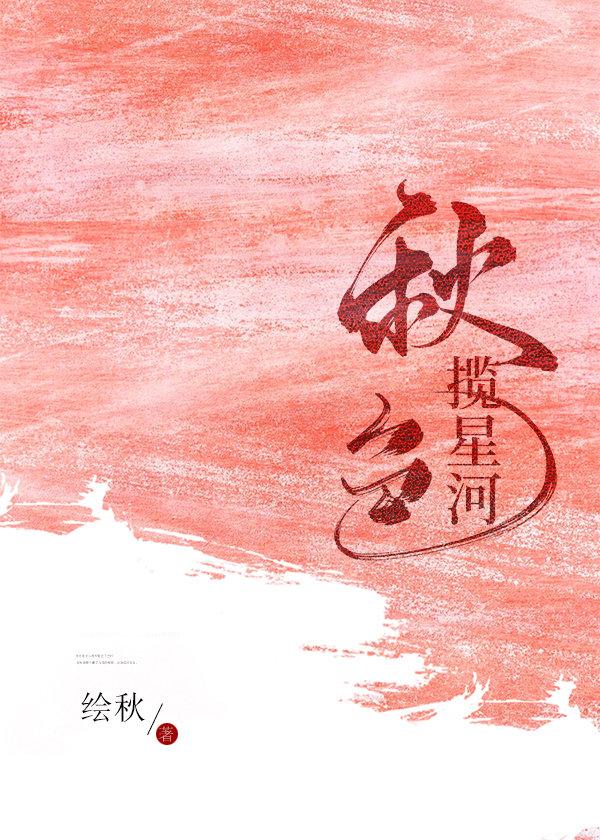52格格党>[二战]日出之前 > 第386章(第1页)
第386章(第1页)
“亲爱的凯瑟琳,”艾伦·杜勒斯抿了一口茶,“我一向不指摘朋友们的私人问题,我只是害怕你们骑虎难下。人们喜欢王子和公主童话故事,你们已经把故事编造得如此美妙,他们就很难从梦境里走出来。”
“任何童话故事都会有收尾的,随着时间过去,人们会淡忘一切,小报也会有新的新闻填充,你知道的。”希尔维娅道,“如果你担心你会和我们俩一起受指责的话”
艾伦·杜勒斯挑了挑眉:“我没这么说。而且很显然——我也不喜欢麦卡锡。”
“还有胡佛,埃德加·胡佛。”希尔维娅轻轻笑了一声,“埃德加·胡佛用一尺半的资料让奥本海默失去了安全特许权,我们可以看看,多少材料能让麦卡锡失去美国民众的信任。”
“显然,不会比那资料多。”艾伦·杜勒斯站了起来,戴上了他用于伪装的大墨镜:“有时候我觉得你会死于非命,凯瑟琳。太聪明的人在我们这个时代一向没有好下场。”
“这是不详的话,艾伦。”希尔维娅提醒他,他自己也属于“太聪明”的那一类。
艾伦·杜勒斯笑了笑,没有收回,也没有否认,他转换了话题:“你知道吗,亲爱的凯瑟琳,如果是我的下属们扮演成一对情人,我会担心他们有朝一日动了真心,以至于把任务搞砸。但我从来不担心你和斯文森搞这套——”
希尔维娅歪了歪头,等着他说下去。
“我比较担心的是,你们俩会各自孤独终老。”他说完这句话,就戴上他的帽子,从咖啡馆的后门走了出去,他坐进一辆漂亮的汽车里,时间掌控得刚刚好,就像只是喝了杯咖啡。
八卦报纸吹起的风潮很快蔓延在整个美国,希尔维娅和斯文森不得不花大量的时间在保镖和司机的簇拥下参加各种各样的晚宴,这把他们俩都折磨得精疲力尽。
“听证会的时间快到了。”
五月份的时候,他们互相提醒,麦卡锡已经在陆军-麦卡锡听证会上丢尽了脸面,人们渴望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一场正义战胜邪恶的结局。
“在那之前,还可以制造一点话题。”有位博士提议,“你们两位有没有考虑过假装订个婚什么的?”
斯文森和希尔维娅的脸色都僵住了,他们俩谁都不觉得要到这个地步。
“我倒觉得没有这个必要。”另外一位学生道,“只需要你们戴着戒指被报纸拍到,人们立马会自我猜测。模糊才能引起人们的想象和热情。”
“这简单一点。”斯文森转向希尔维娅,“你觉得哪个珠宝店好点?卡地亚还是蒂芙尼?”
“我有个更好的主意。您还记得我有一枚蓝宝石戒指吗?”
“别吧,凯瑟琳。我记得我在瑞士见到你的时候,你就戴着了——”斯文森靠在他的办公桌上,“我不认为你和我贫穷到了连枚戒指都买不起的地步。被人识破骗局就不好了。”
希尔维娅来了兴致:“我认为人们不会识破,我们打个赌好不好?”
“什么赌?”斯文森笑了笑,“我认为我们都不缺什么。”
“我认为彩头是什么无关紧要,”希尔维娅摊开手,“一瓶香槟就已经足够了。但我真的很好奇,人们会不会自动填补记忆的空白,甚至模糊记忆的细节。”
“可惜我们的书出得早了。”卡尔·霍夫兰在一边笑道,他指的是前一年他们合作出版的《传播与说服》,“这会是一个经典的课题。”
“如果我们要打赌的话,亲爱的凯瑟琳,我们不妨赌的大一点。”斯文森从他上衣的口袋里拿出一本支票夹,在支票上写了十万美金,又签了名字,“如果你赢了,我就把这笔钱捐给威廷根施坦因慈善基金会。”
“如果你赢了呢?”
“我要求你从国际红十字会安排一次访问。”斯文森双手插着口袋,好像等这句话已经等了很久,“去远东。”
他的“远东”指的是“红色中国”,这对希尔维娅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战后前往苏联的访问已经让她受到了压力,再安排一次远东之行,会让她显得越发□□,但她还是答应了:“当然。”
听证会的前一天,斯文森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和他们讨论这件事情,他的讲稿被改了一遍又一遍,人们一遍遍听他说话,恨不得连他目光的方向都规定好。但年轻的教授提醒他们:“有一点瑕疵或许更好,太完美反而让人们觉得做作。”
他说得很对,吸取了陆军-麦卡锡听证会的教训,主席没有再让麦卡锡一而再再而三地浪费时间,他胡搅蛮缠的技巧在听证会上一件也没有用上。
斯文森在法庭上风度翩翩的演讲随着广播和电视传遍整个美国和世界,他对于麦卡锡的质问更是震耳发聩:“请您告诉我,麦卡锡先生,我以我对数学和真理的信仰答复您的提问,而您呢?您是以政治手段和外交辞令来责问我,参议员先生,除了这些政治上的手段,你还有没有良知?难道你到最后连一点起码的良知也没有保留下来吗?”
那一天没有再有任何质问,记者们向斯文森涌了过去,响亮的掌声从听证会传到美国的每一个角落。希尔维娅也被人们推到他的身边,他们好不容易走出人群,发现斯文森的父母在门外等着他们。
“有时候你真让我伤心,儿子。”那位雍容华贵的夫人这么对他们说,“我竟然是从报纸上得知我最爱的小儿子订婚的消息的。”
斯文森和希尔维娅对视了一眼,都没掩饰住脸上的笑容。斯文森低声在她耳边道:“看来我的远东之行是安排不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