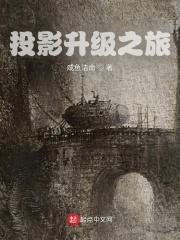52格格党>在青楼捡到江湖死对头后 > 19手铐(第3页)
19手铐(第3页)
白行玉直勾勾地盯着他,稍显僵硬地将手放在脖颈处的衣襟上,丝毫不犹豫,便把上衣一把扯去,丢在一旁床上。
白行玉呼吸又有些乱了,肩头和胸腹轻轻起伏着,少见地显露出几分情绪。
古鸿意平日常跟着毒药师做些打杂的活儿,包扎、换药甚至清创都练习过,算半个小医师,面对过盗帮弟兄们各式各样的伤体,是不羞赧于见身体的,包扎时能做到心无旁骛。
可是,白行玉的皮肤忽然彻彻底底的呈现在他面前的时候,他怔了一下。
他马上明白,为什么白行玉对这件事情如此执著了。
脊背绷的笔直,一张青白宣纸,烙满了青的、紫的、棕红色的,团团的印章般的烙印。
在明月楼的时候,曾经捉住白行玉的手腕,那时,以为他手臂上的青紫只是淤青,养一养,就会好的。
现在才看清楚。
不是淤青,而是黥刑。
“你如意了。”白行玉神情淡淡,做了个口型。
古鸿意感觉心口很压抑,“……是刀旋下的吗。”
说出口,古鸿意便觉得,也许不该问这个问题。
白行玉却毫不在乎的样子,答:“有的是刀,有的是烛台去烫,”说着,他垂头,指一指对应的疤痕,依次介绍道。
“烫红的铁。”
“钳子。”
“这个是……”有的疤,白行玉自己也想不起来出处了,他垂头,指腹摩挲着那里好久,有些惘然。
“他们为什么这样对你。”
白行玉垂眸,摇了摇头,觉得这个问题很好笑。
明月楼的规矩就是这样。花朝节,他卖出去之前,除了……别的什么都可以。
见古鸿意愣在原地,迟迟不动手,白行玉干脆抄起床上的那个银亮的手铐,利落地往自己腕子上一套,“咔哒”合上锁了。
他举起被锁住的双手,举到胸前,锁链摇摇晃晃,银光闪闪。
有些自暴自弃地,他甚至冷笑了一下,然后对古鸿意无声地说了些什么。
古鸿意分不清他说了什么,只看到了他裎身坐在大红缎面之上,惨白的皮肤上是触目惊心的花团锦簇,残缺破败的一个瓷人,完整而健康的只有一头墨色长发,很顺滑水亮,织锦叠绮,别在耳后,垂在肩头。
他说的是:“卖给你了,随你便了,不反抗了。”
古鸿意抓住他的肩头,把他的后背扭到面前来,给他上药时,两个人都很沉默。
古鸿意跟着毒药师,练得手法很娴熟,很快便处理好了他后背的伤口,又缠了几圈绷带。
将绷带的尾端收束住时,古鸿意手轻轻搭在他肩头,古鸿意说,“对不起。”
白行玉摇摇头,有什么对不起呢。
反而,倒觉得自己有些对不起他。
“……我身子好不了,你最好不要期待什么。”
一点黥刑烙印就能吓着古鸿意,而他承受的比这一点耻辱的皮外伤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