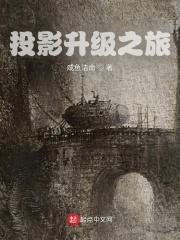52格格党>摧眉 > 黄花瘦(第2页)
黄花瘦(第2页)
等薛严一走,江浔立即把芩云唤进来:“你把窗户小小开一道缝,这满屋药气熏得我头疼。”尤其是要将薛严那厮身上的甘松沉香味尽散了,她闻了恶心。
芩云劝阻道:“姑娘,你还病着。再一吹风,只怕病要更厉害了。”
“不妨事,你开了窗就把床帐遮得牢些。我裹紧被不会着凉的。”江浔再没力气说话,声音嗡哑微弱。
芩云知她主意既定,再难违拗,遂依言照办。只是仍旧怕邪风入体,引得江浔更为病重,开窗不过半刻便重新关严实了。
薛严辅一回房就冷笑一声,朔月这丫头倒是厉害,好声好气说话竟也能将自己激得火气上涌,这匹胭脂马为免也太烈了些。
她比自己还小好几岁,怎得脾气这般古怪执拗,真真是生平没见过这样的女子。
他把侍卫宁则、宁渊都叫来,沉声问道:“你们两个,觉得朔月个性如何?”
宁氏兄弟面面相觑,不知从何说起。过了片刻,宁渊大着胆子说道:“爷,属下看朔月姑娘平时不多说话,但是个极为好相与的人。”。
他想起一事,又补充道:“有一日姑娘问我身契的事儿,瞧着姑娘是十分乐意伴爷左右的。”
薛严嗤笑一声。蠢材,她这是故布迷魂阵呢。要不是那夜见识过朔月气性,这话他就信了。
宁则到底知道些江浔的脾气,遂对薛严说道:“属下瞧着朔月姑娘虽少言寡语,可心下是个极有主意的。不过姑娘善心,对底下人时常照拂,下人都念着她的好呢。”
善心?薛严眼眸晦暗难明,她对众人都和颜悦色,怎偏对他横眉冷对。难道是因为自己断了她在外生活的念想?绝了她独找一人相伴的愿望?
外头有什么好的。她一弱女子孤身在外,不被人生吞剥皮了才怪。
何况薛严自问,自己出身显贵,堂堂正三品江宁刺史,日后行取上京更是仕途不可限量,有多少人削尖脑袋直往他身边凑。论朔月身份来历,以前连公府门槛儿怕都踏不进去,现在得蒙提携了通房,更是高攀。为何一心想将来跟着楞头小子过穷苦日子。
照理说朔月家境贫寒,本应更珍惜眼前富贵。薛严百思不得其解,不信世上竟有如此榆木脑袋。
他感受到自己乱潮般的思绪,自觉不该,遂点了一柱檀香,又捧起一本《弈理指归》研究起来。
晚间用过膳,丫鬟粉蕊叩门来报,江浔的病已经好些了,烧也退去大半分。
薛严本想着人抬了轿立刻把江浔接来。他转念一想,病才刚好些不宜挪动,遂又自行去了江浔院中看望。
府内下人丫鬟俱是伶俐之人,见薛严连着探望江浔,已然明白几分。宁则又来警告一番,众人均不敢多言议论,唯恐丢了刺史府这门好差事。
况且,下人们自觉江浔来了以后体恤府内诸人,眼见她得了薛严另眼相看,日后便更有好日子过了,都是心花怒放。
待薛严进了江浔房中,此刻她背后靠了个苎麻软枕,盖了云绣月蓝团花厚被,斜斜支身看着窗外玉兰,听得动静扭过头来,只见她脸颊消瘦,面色苍白,一双桃花眼无精打采。
病后荼蘼,褪色、却也不失美态。
薛严不禁柔声说道:“你病才刚好些就开窗,小心别着风又引得烧起来。”
丫鬟查颜色知冷暖,闻言立即便把支架一放,合上窗户。
江浔实在恼薛严此人的做派,冷言道:“我自己有数。这几日头脑发闷,病好些了本想看看窗外物景儿,心情一好病能去得更快些。如今大人一来就兀自添乱,可见大人关心不尽不实。”
屋内下人听了江浔这般放肆大胆的说话,俱是身体一震,怕薛严拿他们作阀撒气,连忙垂首躬身急急退下。
薛严知道江浔心中所气为何,他沉默站在床前,打量着江浔紧抿的唇角。
看了一阵,他沉声说道:“朔月,你素来知道爷的秉性。你现在这般,爷也不会遂你心愿。不过若你乖乖听话,等爷娶了亲,便给你放籍出府。”
大家族主母一进门,是要将通房、侍妾都遣散干净的,为的就是体面二字。
江浔听了,知道薛严恪守礼制教条,如今只图个新鲜,不会为她一个奴婢破例,这话有几分可信。
她眼里闪过一丝亮光,脱口问道:“不知爷何时娶亲?”
薛严怎么会告诉她,为避圣上疑心,定好和上京陈家的亲事要推后再议。眼看江浔脸上是藏也藏不住的喜色,心下不快,甩袖便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