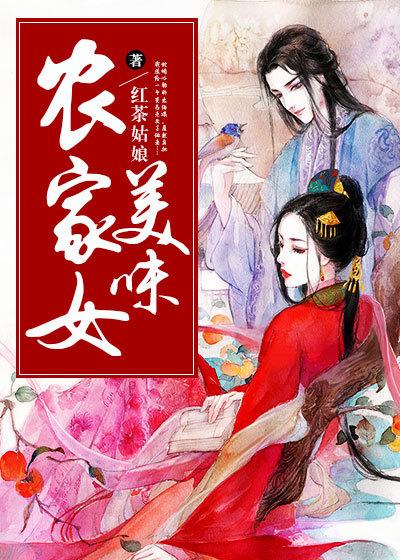52格格党>骗美人喝下忘情水后他忘了我GB > 玉眉峰 13(第2页)
玉眉峰 13(第2页)
“昨夜我二人守了一番,确如师妹所说,他因为还差一人而有所行动,被我二人剑意所伤。”
徐风知抿了口茶,“留痕了?”
二人点头。
“那我现在要是陈常谙,我便——”
徐风知的话还没能说完,高台之上那犹如濒死枯木的人忽然沉默无声地跪了下去,面对芸芸众生,面对悠悠天地。
“陈某有愧。”
茶铺里他们几人对视一眼,他的招数便在这眸光之间轻易破解,几人同时喝了口茶。
徐风知无奈摊手,“他这人,把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打又打不过我们,唯一能走的路子只有先发制人卖惨示弱。”
人群渐渐拥堵到高台下,几乎每个人手上都拿着从他手里领到的饼,焦急地仰着头关切地询问他发生了何事、叫他不必如此。
陈常谙跪在那,低垂着头,“陈常谙命数奇弱,得各位关照活至今日已是侥幸,可我却为了自己这条烂命,背负上许多罪孽。”
这般沉重的开头任谁听了都心头一凝,民众渐渐安静下来聆听他说话,脸上还是写着对他的担忧,全然在忧心这位顶天立地的病弱大善人将要倒下,那么往后他们的诸多苦难谁来管呢。
陈常谙跪着的时候沉重的衣服被架起来一截,看起来既不合身也不舒适,就像披着一个不属于他的壳。
“疫病横行,诸位多受苦难,家中却在此时探查出一古老之法救我性命,说是要在这疫病中身上生疮之人换血给我。”
台下堆积的众人一听一个个都瞪大眼睛,陈常谙将头垂得更低了些,神色凄苦。
“这法子颇为心狠无法言说,他们只好对诸位说是将其接入城中相救相医治,我于心不忍,前去同他们讲清楚,可大家竟都愿意为了我这条命舍身换血。”
“陈某受诸多恩惠,妥善安置好他们的家人后也还是觉得恩情难抵,时常想自己做的不够多不够好,今日借此机会同各位坦白一切,不是求各位宽恕我,而是隐瞒此事心中实在愧疚,夜里不得安眠,每日总想死了一了百了。”
台上的陈常谙神情悲苦,看起来脆弱非常,台下的人虽然神情略有异色,但这事归根结底和他们无关,更别提他们手上此刻还拿着受了他恩惠的饼,好几人率先出声安抚他太过苛责自己。
徐风知实在是听不下去,叩下茶盏,声音清亮地喊道:“怎么听起来模棱两可的,陈常谙,你究竟知不知道此事。”
陈常谙不紧不慢,深望向茶铺几人。
今早在她出现时,陈常谙便一直有在注意她的动向,现在听到她当众质问也不过是印证了他心中所料。
这位灼雪门弟子,并不信他。
徐风知孤身走出茶铺,笑意嫣然,“默许和不知情可是两种情况,陈老板为何不说得再清楚些呢?”
陈常谙露出那种果然没能得到信任的、被伤害的神色,拧眉恳切摇着头,“他们背着我安排好这一切,我知晓时已然迟了……无法改变。”
一双无奈掉着泪的眼睛让人如何不心疼呢?况且还是这么个心性纯良的病弱大善人,一刻前还在不顾个人安危为大家发饼子呢。
“噢,那是身不由己。”徐风知跟着他露出心疼神色,但却稍纵即逝,弯如月牙的眼眸里吹彻寒风,她话锋陡然一转,“那昨天晚上着急忙慌去外城抓人换血的不是你吗?你不还挨了几剑吗?我派剑意,内力留痕。”
她话音一落,掌心凝力凌厉打出一击,陈常谙吃透那一掌风,并不痛,可身上却斜斜浮现出三道剑意。
一道来自昨日的孟凭瑾,另两道则是沈执白和许话宁。
跪着的人背负剑意低垂着头,看不清楚神色,徐风知却仰着头笑眯眯追问到底,“和你换血的人他们每个人都同意了吗?真的都是自愿的吗?”
百姓们不知所措地交换着眼色。
“……黄金百两、家人顺遂一生,”陈常谙的语调听起来很是古怪,似哭似笑,揉着膝盖站了起来,仿若昨日面对相庚时那般温柔地笑了,居高临下的目光笼罩着徐风知,“换你你不愿吗?”
陈常谙铁了心不愿意直面这个问题,但过度的规避就已经是一种回答,任谁都能听懂这话背后的默许之意。
高台下众人神色复杂,交织晦涩的眼神里竟隐隐透着对这位笑意明媚之人的责怪,对徐风知的责怪。
这种责怪甚至更加诡异,徐风知讨厌这种用目光想将她嘴巴封死、想将她整个人钉在地上的阴森。
她顶着那千千百百道犹如寒针飞来的视线向前踏进一步,沈执白和许话宁紧随其后,众人轻蔑退避,她视若无睹,平静淡然启唇道:
“他说的没错,只要他想,黄金千两万两,总有那么些人自甘站出来和他换血的。”
她抬眸,眼里蒙蒙雾气一瞬泯然,黑白分离得彻彻底底,盯得久了总觉得像一点光一团火,她厉声质问:
“但陈常谙,我就问你一句,为何这疫病出现得这么巧呢,这法子要的是疫病中生疮之人,这疫病怎么倒像是为你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