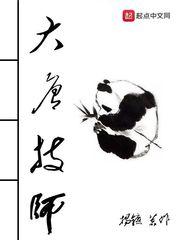52格格党>我家的女人 > 第3章(第3页)
第3章(第3页)
尽管如此,我跟张岩他们谈到女人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常跟他们说起我妈以前被许多男人上过的事,也许是出于一种炫耀或类似暴露阴私的心理。
开始我只跟他们说我亲眼看到过我妈跟男人性交。
他们知道我爸妈离婚了而且我妈刚去医院生产出来,立刻就猜出那个孩子不是我爸的,缠着要我详细说内情。
我刚开始不肯说,后来禁不住他们软泡硬磨就慢慢都说了,包括小时候我妈被农民和狗轮奸,到后来被同学的父亲老王强奸,再到为文主任胁迫被许多男人奸污的事情。
讲到后来的香艳麻将局时他们都纷纷瞪大了眼睛,而我很有一种快感。
我也是出于这种心理才把我妈的经历写出来的。
他们后来看到我妈的时候一个个眼神都怪怪的,好象要透过她身上的衣服看她的裸体一样。
不记得是谁开玩笑似的说过“什么时候把你妈弄来大伙玩玩”,我当时也不当回事的随口答应了。
我以为是玩笑的事,有几个同伙却颇为上心。
他们显然对我妈的成熟肉体颇感兴趣,背着我周密计划了一番,到最后木已成舟才告诉我,而且威胁我说如果不跟他们合作,就把我妈的事用小字报贴在学校里。
另一方面,他们又向我保证,只要我合作,一定不会伤害我妈,而且我妈事后也不会知道。
甚至他们说我可以先玩我妈。
他们开出的条件颇为诱人,要我做的也很简单,策略是迷奸,就是由我把一些药粉想办法让我妈喝下去,然后在她喝下药粉的两小时内把她带到一个特定的地方,他们会用一种特制的香在两种药的作用下把她迷倒,这种香只对喝过药粉的人起作用。
凑巧那段时间我妈刚刚生产过后老是腰膝酸软,每天都喝中药,一般一副中药她中午喝一服,晚上再喝一服。
经过反复研究,我们决定在我妈中午那服药里下迷药,然后把她骗到张岩的表哥开的自行车铺里。
那个自行车铺离我们家不远,在一条偏僻的巷子里,平时行人不多,也不引人注意。
张岩的表哥叫严森林,是个三十出头的光棍,脸上一条三寸长的刀疤,平时老是一脸凶相,一双眼睛总是阴冷阴冷的。
我刚开始还担心他会不会帮我们,其实后来才知道那个姓严的实际上是黑社会的,迷奸我妈就是他和何慎飞两人在幕后主使。
计划的过程就不多说了。
初夏的一天中午,我回家吃完我妈烧的饭,趁我妈出门倒垃圾的机会把贴身藏着的一包棕色粉末倒进我妈熬好的中药里,还用筷子搅拌了几下,然后等我妈回来看着我妈喝下一大碗。
我妈还说“今天的药怎么有点苦”。我心里暗笑,跟我妈说“难道中药不都是苦的吗?”我妈摇摇头。
出了家门后我径直把车推到严森林的车铺里,他熟练的把前车胎放了气,把内胎拉出来装做在补车胎。
我则一路跑回家去,气喘嘘嘘的跟我妈说“我的自行车没气了,在那边的森林修车铺补轮胎,很快就好。我先上学去,你一会儿去学校的时候去取车顺便付钱可好?”我心里就想说你一会儿要去让我们玩玩你的奶子和屄可好?
我妈爽快的答应了。
我装模作样的再次出门,在巷口绕了一圈就转回来,躲到森林修车铺的后面楼梯间里,那里面已经有六个人,包括张岩和其他两个学校里的同伙,还有何慎飞和两个不认识的人。
严森林在前面照顾铺面。
张岩跟我说介绍说那两个不认识的人都是这里附近治安联防队的,一个姓程,一个姓李,都是何慎飞的朋友。
铺面上只有严森林一个人。
楼梯间有个洞,可以看到外面的情况。我们又等了一会儿,我妈还没出现。
一个叫文渊的同伙有点沉不住气了,问我“你妈会不会来”我说会,其实心里也没底,眼看快两点了,过了两点半那药可能就要失效了。
我妈的在学校是下午两点半有课。
姓程的联防安慰我们说“小孩,别着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正说着,张岩轻轻嘘了一声,小声说“来了!”我挤到洞口往外看,果然我妈远远的走来。
她穿着一件格子花衬衫和黑裙,皮鞋敲击水泥路面的声音由远而近。
我看到严森林顺手用手里的烟点燃了脚边的一盘象蚊香一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