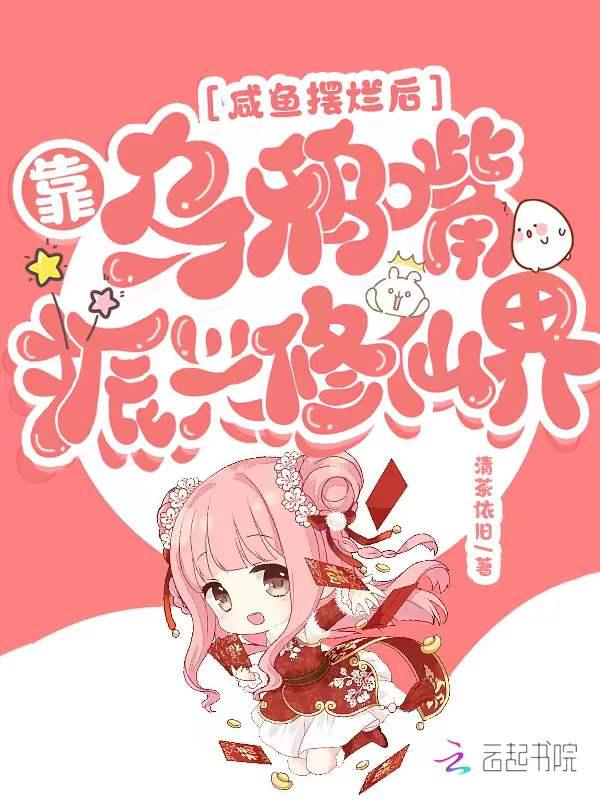52格格党>嘿我还真就作了一辈子[年代] > 8088(第23页)
8088(第23页)
周六一早,靳延准时赶在闹铃响起前睁开了眼睛,他伸手将没发挥过几次作用的闹钟关掉,眉眼间还带着倦意。
沈意欢过去十多年都是跟随着军区战士的作息生活的,这个习惯自结婚后被靳延打破,而等他们搬到军|委家属院这边以后,更是连铃声都没得参考了。
但好在还有靳延,他虽然有个爱睡懒觉的小嗜好,但绝不会在工作日睡迟。沈意欢只要在前一天晚上和他提前说好起床时间,他就能准时在那个点叫醒她,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
保险起见,沈意欢也会设闹钟,但靳延总能在闹钟响起之前就及时醒来,再由他亲自叫醒沈意欢。
虽然按靳延的说法是,怕闹钟声太刺耳吓到她,但沈意欢却觉得靳延的叫醒服务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他是个生命力很旺盛的人,连胡子都比一般人长得更快些。无论头一天刮得多干净,一晚过去,定然会冒出一片青色胡茬。
而这胡茬,也是靳延叫醒沈意欢最有力的手段。
但最近,靳延却越来越难以舍下心叫醒沈意欢了,看着她靠在自己怀里睡得又沉又香的样子,靳延就只想把所有的一切都关在门外,任她睡个够。
可是不行,靳延不可能拖沈意欢的后腿,无论初衷是什么。
他太知道沈意欢有多珍惜这个机会了,也明白这个机会对沈意欢意味着什么。
他还记得两人互通心意那晚,沈意欢说她的梦想之一就是跳给全国各地的人看,跳给戍边战士、田间农汉、山中幼童看
可她刚刚才踏上圆梦的第一步,却又被不可抗的因素绊住了脚步。想起这两年沈意欢没有伴奏的起舞,靳延就觉得心疼。
好在转机终于来了,这部电影,就是沈意欢的事业回到正轨的第一步。
靳延也相信,沈意欢迟早有一天会不用再借着荧幕、真真正正地跳给全国、甚至全世界看。
想到这里,靳延低头碰了碰沈意欢的颊侧,温柔地唤她,“老婆,起床了。”
沈意欢将头往靳延怀里埋了埋,完全没有要醒的意思。靳延看了眼时间,干脆把她半抱了起来,利落地拉下她的睡裙,又探身拿起了她的内衣。
论起脱,靳延很熟练,但穿还是第一回,但两者是共通的,这一步并没有耽误靳延太久。
他扣好扣子,长臂一扬,床头柜上的衬衣也到了手里,也是这时,他才发现沈意欢已经醒了,正睁着她那双还带着困意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早安老婆。”靳延弯了弯唇,很是惊喜她今天的乖巧顺从,她很少在清醒的时候允许他这样做。
将余下的衣物也替她穿好,靳延正准备伸手抱沈意欢,沈意欢却先一步挂到了他身上,声音懒洋洋的,“好困,不想走了,哥哥。”
沈意欢很少叫靳延别的什么,不像靳延嘴里总是有各种稀奇古怪又饱含爱意的称呼,她更喜欢直接叫靳延的名字,像哥哥、老公、教|官这种词都得靳延逼着哄着才肯叫一两声。
靳延一边往卫生间走,一边拍了一下她的屁股,哑声警告,“别招我。”
沈意欢弯了弯唇,坏心眼地往下滑了滑,果然撞上了一大包,她幸灾乐祸地笑出声,“就招你。”
放在以前,靳延绝对要让沈意欢为她的挑衅付出代价,但现在,靳延就是只拔了牙的老虎,啥也不敢做。
将挤好牙膏的牙刷塞到她手里,靳延才没好气地咬了咬她的颊肉,很轻很轻的那种,连一点红痕都没留下。
他哑着声,“你尽管作,我都给你记着呢,电影总有拍完的那一天”
沈意欢笑着躲了躲,含着牙刷口齿不清地宣布了一个“噩耗”,“我昨天听见团长说,制片厂让团里年终汇演不要排我的班,过年前不一定能拍得完。”
靳延被她有恃无恐的样子气笑了,恨恨地掐了掐她的脸,“你就欺负我吧。”
用毛巾擦干脸上的水,沈意欢睁眼就从镜子里看见了身后正在刮胡子的丈夫。
他站在自己身后,单手撑在洗手台上,将她整个人都圈在怀里。
靳延以前用这个姿势干过很多坏事,即使这会儿只专心地剃着胡须,也依旧散发着不输那些时刻的男性魅力。
他侧仰着下巴,刮胡刀顺着他近乎完美的下颌线条滑下,发出快慢不一的沙沙细响
沈意欢眨了眨眼睛,看着靳延将最后一点白色泡沫刮下,忽然抬手搂上了他还赤着的肩,颇具暗示意味地盯着他的薄唇。
靳延眸中闪过一丝笑意,却没有像往常那样体贴,反而拍了拍她的腰,“怎么了?小心点,别把腰扭了。”
因为是被靳延抱到卫生间来的,所以沈意欢洗漱时是站在靳延脚背上的,这会儿姿势的确有些别扭,但对于沈意欢来说根本不算事。
沈意欢知道靳延是故意的,他是世界上除了她自己之外最熟悉她身体的人,他也将她身体的柔韧利用到了极致,仗着她的柔软达成过不少坏心思。
他这样,不过是想让她自己张口求。沈意欢才不惯着他,转移目标,猝不及防地咬了咬他的心口。
唇下的肌肉一瞬间绷紧,但也晚了,沈意欢满意地看着自己的杰作,圆圆的牙印不偏不倚地将那颗小红豆圈在正中间,很对称的美。
正欣赏着,沈意欢忽地被人抬起了下巴,对方刚一贴上,就气势汹汹地夺走了她的全部呼吸空间,示威般地逡巡她作乱的牙尖,连舌、根也被口允得发麻
“唔。”沈意欢本就疲惫的身体彻底软了下来,只能靠着靳延握在她腰侧的手勉强站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