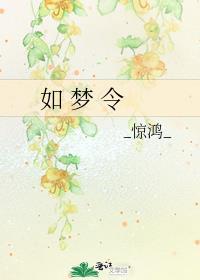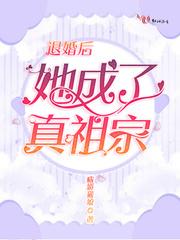52格格党>落榜当天,娶了个首富千金小娇妻 > 第一百五十九章 殿试之策(第1页)
第一百五十九章 殿试之策(第1页)
世人不知,他并非寻常士子,而是天子心腹之人。沈墨自幼便聪慧异常,学问渊博,朝堂大员早已看中其才华,将其暗中培养。如今他的身份虽是士子,实则是天子暗设于士林的“天监”,专司监察士子、翰林乃至部分朝堂重臣,甄别贤愚,防止奸佞之徒借功名入仕。而姜孟川,显然是一个异数。会试夺魁,本应是士林荣耀之事,可他却是个商贾之人!更有甚者,他在应天府的商道势力日益庞大,甚至能与权贵交往。这样的身份,已然引起朝堂中人的警觉。“他若只是个普通士子,或许此番殿试便是他的登天之阶。”沈墨低声喃喃,意味不明地笑了笑:“但如今……这座天梯,怕是要有人动手折断了。”他随着他话音落下,殿试正式开始。皇帝端坐龙椅之上,目光锐利,气势森然。“传旨,殿试试题——”礼部尚书展开卷轴,朗声道:“如何振兴大乾商贾,使其不妨碍士道纲常?”此话一出,殿中士子皆是微微一震。一瞬间,众人交错的目光,不约而同地投向姜孟川。这是在考商贾之道?这是在考姜孟川?!不少人眼底泛起冷笑,纷纷起了看热闹的心思。圣上这是要让姜孟川“自证清白”吗?若他答得不好,士林清流必定群起而攻之,贬斥他“不知纲常”!若他答得太好,难免让天子对他起疑,如何能安然入仕?!这道题,是皇帝亲自设的局!不少人心思电转,而沈墨却眯了眯眼,轻笑着开口说道:“这道题……倒是有意思。”他缓缓抬头,看向姜孟川的方向。他心中倒是好奇,姜孟川如何应对?与此同时的大殿中,姜孟川看着考题,微微一笑,眸色深邃。他提笔,沾墨,落字如风。“商贾与士道,并非对立,而可互为依托,共济国势……”笔走龙蛇,字字珠玑。他在文中提出,陛下若欲富国强兵,绝不可轻视商贾。商贾不仅是国税来源,更是连通天下货流的枢纽,若能合理规范,定能助国兴盛。更重要的是,姜孟川不仅援引古今治国之策,更结合自身商道经验,提出“商贾士道共济”之策,言之凿凿,令人折服。当最后一笔落下,姜孟川收笔,目光沉静,毫无波澜。可殿中不少人,已是神色复杂。沈墨望着那张宣纸,轻叹一声,眼神中流露出些许感慨。“这篇文章……恐怕要震动朝堂了。”天子震怒,还是欣赏?随着诸位学子停笔,试卷被送入御前。金銮殿上,天子翻阅姜孟川的文章,目光渐深,指尖轻敲龙案。“此子,倒是有趣。”殿内无人敢言,唯有翰林学士沉声道:“陛下,姜孟川此策,实有可取之处,然其毕竟商贾之身……”话未说完,皇帝便嗤笑一声,放下奏章,冷冷扫视群臣:“朕且问你们,若此策当真可行,便是寒门士子所言,还是商贾所言,又有何妨?”殿中众人纷纷低头,不敢再言。皇帝嘴角微扬,淡淡道:“朕本意乃求治国之才,非论门第。”“将他召来,朕要亲自问上一问。”除了姜孟川外,皇帝随口另点了旁的几个士子,颇有几分陪跑的意味。沈墨在一旁垂眸,暗自思索。他看向天子眼底那丝意味深长的神色,知晓……姜孟川,入圣上之眼了。自大乾开国以来,殿试向来乃国之重事。文章出色者,可得天子亲自策问,殿前群臣共评,得中者封赐功名,甚至有可能入阁议政,可谓一步登天。在众多目光的注视下,姜孟川神色平静地走入殿中,端正叩拜,向皇帝行礼。“今日殿试,诸卿皆天下英才,既经会试选拔,想来学识已得考验。”“虽然你们方才都有交上答卷,但写下和实干终究是不同。”皇帝的声音不怒自威,微微颔首开口说道:“朕出此策,乃为考汝等之才,亦为观汝等之志。”做官可不仅仅只是写写画画就行,口才也是一条重要的评审标准。“朕问尔等——大齐商贾之道,何去何从?”随着皇帝话音落下,一众贡士面露思索之色。这道题目,比往年任何一道策论都要锋锐,从方才礼部尚书公布考题的时候,他们便察觉到了。若是说方才落笔还有思索的时间,但现在真的要说出,可就是真的考察他们肚子里有没有墨水的时候了。商贾之事,向来不是科举的主考重点,朝廷历代以农为本,商道虽不可废,却非士人议论之重。但姜孟川则是神色淡然,目光微微一闪。他早在备考时,便已思考过类似的问题,而他心中所想,早已成文。而现如今,皇帝想听的很明显不是自己方才写在考卷上的浅显之言,而是详细的策论。皇帝的目光扫过众人,忽然开口:“姜孟川。”殿中目光齐齐看去,露出几分果真如此的神色。果然,最受关注的那个人,最先被点名。“臣在。”姜孟川拱手出列,步伐沉稳,不卑不亢。皇帝看着这个年纪不过二十出头的青年,眼神中带着几分意味深长。这个年轻人,在短短一年之内,从一个寒门士子,成为会元,又在应天府翻手为云,搅动商界风云,如今又站在了这殿试之上。“你可先言。”听到皇帝这话,姜孟川微微躬身,朗声道:“臣以为,商贾与士道并非对立,反可相辅相成,助国兴邦。”此言一出,殿中许多老臣目光微变。这番论调,与当朝士林固有认知大相径庭,甚至颇有几分离经叛道之意。虽然感受到了朝中大臣们隐隐约约的几分不满,但姜孟川依旧神色不变,继续说道:“士者,理政安邦;商者,流通财货。”“盖商贾者,流通天下之财货,使南北之利可互济,东西之需得调和,促使国运通达,民生丰足。”:()落榜当天,娶了个首富千金小娇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