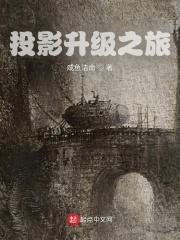52格格党>旧情难了:迟爷乖乖跟我走 > 第 265 章(第2页)
第 265 章(第2页)
靠在沙发上,手指迅速的换了张手机卡,然后看了眼屏幕上面积了三个月的消息,随便点了两条回复了一下,就扔在了一旁。
他发了条信息给蒋鹤,让他找找那条消失了的红绳。
蒋鹤似乎不怎么当回事,还反问了句,“不就是个十块钱好几根的绳子么,我赶明去批发市场给你带一箱子来,你每天换着带。”
迟倦只发了一条消息,对面就像是噤了声一样,气都不敢出一下。
【迟倦:姜朵送的。】
他发完了这条消息后,关了手机,沉沉的靠在沙发上,手指摸着腕上的脉搏,一阵一阵的,像是在告诉他——你还活着。
可又有什么用?
迟倦垂眸,手指在胸前的肋骨上一根一根的划过,像是在雕琢什么精美的瓷器一样,目光缱绻,深沉。
他知道,自己的前二十年活得很失败。
从前的他能为了区区十万块,而跟红庭的酒鬼七爷对赌,赌什么呢,就赌七爷没输过的酒量。
击败别人最引以为豪的事情,是迟倦觉得最刺激的事。
他从没有说过,其实迟砚长的占有欲和控制欲堪称变态,无论是女人还是儿子,他都要捏在股掌之上,肆意玩弄,随心拼凑。
在迟砚长的价值观里,女人无须太过天才,最好是一辈子愚蠢下去。
所以迟砚长费尽心机的打压颜宁,甚至在折磨她后,还屡次偷摸的请心理研究者来对颜宁进行干扰,不仅如此,更是将所有污水泼在颜宁身上。
只有把颜宁弄疯,迟砚长才能彻底安心下来。
不得不说,迟砚长成功了,他成功地把颜宁塑造成了一个疯癫、病娇、又偏执的人。
都说,儿子总是很像父亲的。
更何况,是一个朝夕相处、又血浓于水的父亲?
也许,在迟倦察觉不到的内心深处,也住着一个迟砚长一样的刽子手,要不然,他又怎么敢杀人,要不然,他又怎么会如此理解颜宁的一切?
可偏偏,兴许是那张皮囊的缘故,迟倦只需要稍微掩饰一下,就能伪装成一脸无辜又无害的模样。
迟倦堪称顺从的在迟砚长的眼皮子底下活着,从来不张扬,从来不反抗。
他在等一个机会。
迟倦撕开了香烟包装的塑封,精准的扔进了垃圾桶里,修长的手指掐住烟尾,突然很想念在红庭里的感觉。
音乐、酒精、低廉的香水味、还有身材各异的女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