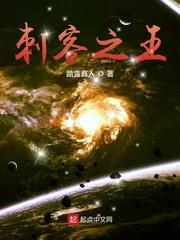52格格党>似蜜桃 > 第65章 第六十五章(第2页)
第65章 第六十五章(第2页)
虽然萧明彻下头还有福郡王、康郡王两个已成年的异母弟弟,但那两位郡王因生母出身低微,性情又温和,一向都谨小慎微,无甚做为,齐帝从未将他们放在心上。
如今乱象突生,齐帝猛然发现,膝下已成年的儿子里,就只有萧明彻这一个稍成气候的。
虽然萧明彻不是他最满意的儿子,但他如今只有这一个选择。
他已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再去扶植别的儿子了。
人有时候很可笑。
如今他只能将希望放在萧明彻身上,便好像忘了从前是怎么对待萧明彻的。
或许也记得,但他别无选择,只能强行父慈子孝。
对齐帝难得的和蔼示好,萧明彻心中冷冷哂笑,表面却平静乖顺:“谢父皇隆恩。”
李凤鸣曾说过一句话:亡羊补牢,羊毕竟是没了。
萧明彻深以为然。
对他而言,“父皇”这个称谓,与“陛下”没有区别。
在他心里,自己从小就父母双亡。面前这个苍老的男人仅仅是君王,不是父亲。
无论齐帝对他好或不好,真心还是假意,他都无所谓的。
太子在恒王府算是捅了马蜂窝,局面非常棘手,齐帝虽怒火攻心,却并没有十分慌张。
近些年太子和恒王斗得虽厉害,但在国政朝务上各有强项,齐帝便只把控大局,将具体事宜交托给他二人去出面坐镇。
再加上齐帝从去年起反复发作头风症,目力大损,就更像个不问事的虚弱老者了。
可事实上,抛开人品德行不谈,他做为一国之主,还是有几分本事的。
“照你看来,该如何处置太子?”齐帝拿起象牙箸,眯眼睨向萧明彻。
萧明彻垂眸摇头:“储君之过,当由圣心裁断。”
他这么有分寸,齐帝很是满意。“那就让太子继续在东宫养病吧。”
南境与宋国大战在即,当前若废太子,后果难料,几乎等同赌国运。
萧明彻微微颔首:“那恒王兄的死因,对外如何说法?”
“勾连金吾卫中的叛逆狂徒,意图行刺太子,事发后自尽。宗正寺立即结案,丧事从简,恒王府女眷以戴罪之身继续圈禁。”
齐帝摸索着夹了一筷春笋肉片,细嚼慢咽起来。
“至于后续该当如何,朕想听听你的想法。”
萧明彻道:“卫兵对那种毒略知一二,可命他协助御医署加紧研制解药。待恒王府女眷身上的毒都解了,父皇再行大赦。”
先发制人定了恒王的罪,恒王遗孀们自要连坐。这棒子敲下去,世家再怎么也会安分一段时日。
等到她们的毒都解了,齐帝再做好人行大赦。如此恩威并举,就算世家往后得到什么风声,明面上也不会跳太高。
这样虽比齐帝原本打算的“全数问罪灭口”要麻烦,但有人味多了。
“你啊,心软,”齐帝哼了哼,却没有反对,“这法子倒也可行。不过,后患无穷。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若世家将来得知真相,照样可能借机抱团闹事。到时该如何收场,你可想过?”
世家坐大,这事从齐帝祖父辈起就是皇室一块心病。齐国三代帝王都在不动声色引庶族入朝,试图逐步消解世家顽固根基,但成效甚微。
此次出了恒王府这桩事,齐帝不担心别的,最怕就是没有安抚好各家、埋下动荡隐患。
国政朝务如棋局,事无大小,都该走一步看三步,谋定而后动。
他已只能指望萧明彻,有些事便得一点点教起来。
然萧明彻已在他不注意时独自长大,教不教的,好像也就那么回事了。
“此次南境国战后,若蒙圣恩拔擢,军方便能多出许多庶族将领。”
这话是从萧明彻口中说出来的,但根本就是齐帝的心思。
齐帝既惊讶又欣慰,噙笑点头,又问:“那朝堂呢?文臣仕途被世家把持许久,此事经你高祖父、祖父与我,萧氏三代绞尽脑汁,都未能完全破局。”
“那是因为不曾大破,自无法大立,”萧明彻从容应道,“若能效仿夏、魏,改夏望取士为文武科考,可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