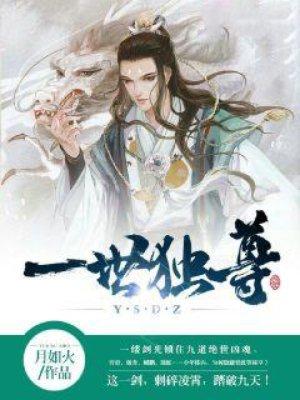52格格党>天时牡丹 > 番外4明丘宣(第2页)
番外4明丘宣(第2页)
她又笑了。
她处理好伤口就走了。
我跟姨姨送她出去,她脚尖点地,就往空中而去,她在空中回头,风吹乱了她的头发,发丝像一只抚摸着她脸的手,她说:“走了!谢谢!”
“再见沈神君。”
“再见沈神君。”
这次她没有飞天而去,她以另一种方式离开了。火尽之后,有三只鹤在空地上盘旋,最终也飞天而去了。
我还在这儿,我不能离开妖界。
我还有问题,还尚未向她追问。
她爱我吗?吻是附加于安抚我的,还是她本就想吻我?她看向我眼神,总是格外温柔,让我全然忘了她是个肃杀冷峻的掌刑之神。
她的情意显得我爱欲的肮脏。
可我没法阻拦我对她的欲望。
我拼命装得纯粹,爱得纯粹,某一天我发现,我的意欲仍然投射在她身上,以她命名,久久地刻在我的心头,深入骨髓。她对我一再回应,但我不曾认为她向我低过头。
她对我,像神怜悯众生的恩赐,见我求得可怜,她便转头关照我。
她的爱如细水,涓涓慢流。我自以为我有如城池般固若金汤的完整自我,足以接住她给我的涓涓爱意,哪怕是为了保持体面,不戳穿她勉强的事实,我也能稳稳地接住她的情意,直到我站在我的灵魂之后反观自己,我才发现我不过是个筛子,是个竹篮,我拼命接住,也不过是一场空。
我想留下我与她相处之中,存在过的具有实体的东西,好让我切实感知到她曾存在于现实中,而不是一场我多年妄想的幻梦。
后来我还是把那些有关于她的东西全都烧了。
如今,只剩下记忆。未向她追问的问题,我反过来追问自己,我独自在无人处向自己拷问,反复思考我们相处的细节,妄图找到一点儿证明她在乎我的证据。
是我太贪婪了吗?
是我太贪婪了。
我要她与我结契。
她身边只能站我一个人。
不,使她嫁给我对她而言是一种残忍。
她死了。
天边夕阳渐冷,仿若多年前的旧事还萦绕耳畔。
「“嗯!不会让你失望的!”
“宣儿,没礼貌,叫沈神君。”」
沈神君,
我于妖界各处飘荡的新生灵气中找你。
我想念你。
二、虎爪弯刀
虎爪弯刀,是他被拔下的五爪。
他的骨剑,是他被拔下的尖牙。
妖界,战时,明丘宣父母已去。
王族,徒留下瘦弱的君王和她未成年的侄子。
根基未稳的王君自保尚且不足,侄子是更难庇护。对王权的渴望会迁怒于没有亲缘关系的孩童。明丘宣躲避再三,还是被谋逆之徒逮去。
乱贼将他踩于雪地里,殴打直至现出原形,贼人拖着他的后腿,跨坐在虎背上,像拉雪橇一样拉着他,绕着雪地走了整整两炷香的时间。
其间,揪耳扯脸,往虎嘴里塞下寒冰,还觉不够,拖他至薄冰的湖面之上,把麻绳套上虎头,让体温融化薄冰,一脚滑入寒凉刺骨的水里,使脖子上的绳子瞬间拉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