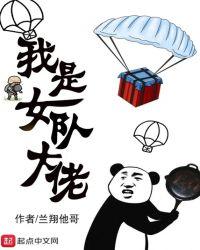52格格党>绝对沉溺 > 第63章(第2页)
第63章(第2页)
“没事了。”
谢淮希把头埋在他肩胛骨处。
将眼泪抹在他里面的卫衣上,哭着,但是没有声音。
傅冕钊顺着他的背,语气中带着歉意,“是我的疏忽,上次底下人办事不彻底。”
“不是你的错,也不要怪他们。”
是有邪念的人的错。
谢淮希伸出手,抱住了他。
“傅冕钊。”
“嗯。”
“我害怕。”
谢淮希是第一次近距离感到恶心。
那种来自生理和心理上厌恶,让他不寒而栗。
“我在这里。”
谢淮希抱紧了一些,“嗯。”
傅冕钊带给他的安全感,从十年前到现在,依旧没变,在他身边,总能感到心安。
“腿怎么了?”
眼尖如他,一下子就看到了谢淮希正在流血的小腿。
是刚才的玻璃划破的。
谢淮希这才想起来茶水间里的狼藉。
傅冕钊将他放在一旁的懒人沙发上,问,“医药箱在哪儿?”
谢淮希指了指一个很小的柜子,打开来看,里面有很多常备药品,都是新出产的。
傅冕钊半蹲在他面前,抬起受伤的左腿,不同于小时候那遍布丑陋伤疤的腿,现在的小腿莹白光洁,匀称漂亮。
只是有两道细细的伤口正在出血。
消毒清理后,傅冕钊贴了两张创可贴上去。
“谢谢。”谢淮希有些别扭地把腿收了回来。
“在哪儿?我去收拾。”
看这伤口,傅冕钊也知晓发生了什么,没有什么可以瞒过医生。
尤其是医术高超的医生。
“那里。”谢淮希指了指茶水间的位置。
他就坐在一旁看着傅冕钊将那一片区域清理干净,然后又倒了一杯热花茶给他。
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但莫名觉得内心的一块空缺被补上了。
至少,他不孤单了。
“你今天晚上可不可以晚一点再走?”
他害怕又出现那种情况,彻夜的敲门声像是催命符一般……那个噩梦般的夜晚,给他留下了极大的心理阴影。
“谢小公子,你就不怕我?”
这个问题的答案几乎是呼之欲出的、肯定的。
他从来都不怕傅冕钊。
以前不怕,现在也不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