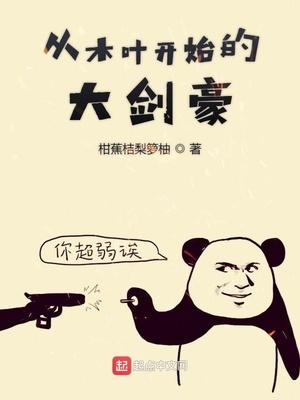52格格党>桃色镜头 > 第112章(第1页)
第112章(第1页)
喻呈明白了,有点不好意思:“怕你干着急,潭宁栩那我打电话问了,我们这边没那么严重,都没事。”
“真的?”
“真的!”
微不可察地停顿,兀自藏去一些细节,比如日日喷三遍的酒精,稀缺的口罩,售罄的药店……最后又自省:“下次我不发这么多条,尽量把话攒着合在一起,按一条发。”
谁在说这个。潭淅勉想,真是傻子。
“喻呈,还有个消息。”
听语气就直觉不是好事,喻呈在电话那端缓慢地“嗯”了声,好似在做心理准备。
“因为这个事,影响进度,我们拍摄周期估计要延长。”
“延多久?”
“目前说还要2-3个月。”
双双默了一会。
违约金高昂,也不是潭淅勉想回就能回的。
还有没明说的一点是,他很不喜欢被等待,被遥遥无期的等待更为致命,他其实就想说别多费心思了,结果发现喻呈很快重振旗鼓——
“没事。就3个月嘛。你做好你的工作,我在这边做好我能做的。”
说这话的时候以为3个月飞快,也幻想过也许这个病毒的影响会在某一天一觉醒来突然消失,谁也没料到这个人人自危的冬天格外漫长,有些人被迫留在旧年,去不到新年。
听过太多坏消息,或许也有好的,一些从石隙里钻出来的希望,比如随着对病毒的了解,在各方的努力下,防控迅速进入正轨,比如大家捐款、捐物,分享口罩与药物,做力所能及的,一起等待春天的降临。
喻呈也报名成为志愿者队伍中的一员,在社区外帮助维持采样秩序。凌晨一点才做完消毒往家走,天寒地冻,防护服里闷出的汗此时又被风吹冷,冰着脊背。回到家先洗澡,洗完澡往床上一躺,感觉四肢都要散掉。
寂而沉的夜,四周黑暗,他昏沉头痛,想明天怎么样,会更好,还是更坏,想自己很久没有出去拍片,更没有出去旅游,又想潭淅勉,可累得无法思考,算不出时差,最后发了一条朋友圈,是自己穿防护服工作的照片。附文:生日快乐。
放下手机正要睡觉,弹出一条视频邀请,竟然是刚刚在想的人。
点开后,画面先晃动,能看出那边更亮,炽烈的日光从缝隙里钻出来跑进眼睛里,镜头突然一下摆正,好像人肩膀上背着什么信号增强的设备,又看到一双马丁靴,踩着沙砾咯吱向前,方向再往上打,霍然望见广袤黄沙尽头一轮红如血的落日。
潭淅勉的声音不稳,喘息,可见爬得很高,才得以望得足够远。
“我们寿星是不是没睡?”他说,“给你看撒哈拉的日落。等太阳完全消失以后,这里就会非常非常冷了。”
他语气随意,像是自己日日能见的风光顺便同他分享。但对喻呈来说,是之前一直闭塞的情绪突然找到出口。他忍住要流泪的感受,紧盯着那枚将落的宏大的太阳,这个未开灯的房间好像瞬间被点亮了,四面逼仄的墙壁都倒塌,之前那些沉重的、慌乱的都暂抛脑后,他好像一下越过了什么,变轻盈,变滚烫,向热烈的光飞驰而去。
“潭淅勉。”他眼眶热,不知道在画面里明不明显,“你好不好?”
“这边还好。”潭淅勉回答,“摩洛哥可能有病例,他们也不是很注意防护,现在中国大概是最安全的。不过好在阿尤恩城市太小了,比较闭塞,暂时还没听说有人感染。”
有一丝庆幸,又觉得像风中护着一簇岌岌可危的火烛,盼他平安,又时不我待。
喻呈咬了咬嘴唇:“等你回来,我想跟你说件事。”
语气一郑重,潭淅勉就猜到方向,他笑了一声,只能懂装不懂,四两拨千斤同他开玩笑:“别吓人好不好,你这语气简直像你怀孕了。”
喻呈的耳廓染上红晕:“潭淅勉!”他急迫地纠正:“我想问你要不要在一起。”
说完以后一切都安静下来。似乎只能听到撒哈拉的沙砾被风吹落的声音。
其实是有点尴尬的。但喻呈想,说都说了,也别管对方需不需要时间,需不需要空间,他反正一直是主动的那个,再想后果没意义,今天的这轮太阳落下去,明天升起来就是新的,上一次表白失败,不代表今天还会失败。
所以喻呈继续说道:“我之前觉得不急,可以等,可是现在经历了这些,看了这些,我觉得时间有限,我想问问你要不要和我在一起。”
潭淅勉把镜头转过来,对准自己,他在沙堆上枕着手臂躺着,背景是染上霞光的靛色天空。
面对这个问题,他安静了一会:“我本来没想现在说的,既然你讲到这个——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你要先听哪个。”
喻呈心里一悸:“坏的吧。”
如果坏消息说完,好消息仍旧是好消息,那么坏消息就不算太坏。
潭淅勉笑着叹气:“你这人。可不可以先听好的。”
不待喻呈答应,他接着说:“好消息是拍摄进尾声,还有一个月结束,不会再延期了。”
喻呈不敢喜悦,紧接着问:“那坏消息呢?”
“坏消息是,由于现在的特殊情况,总公司资金紧张,决定撤回在中国市场的投入。”他缓慢地说,“我这边结束后,可能就要回美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