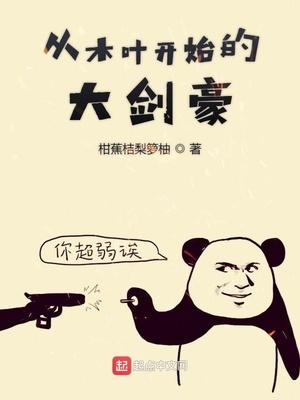52格格党>折姝 > 126 第 126 章 定亲(第1页)
126 第 126 章 定亲(第1页)
元贞二十九年冬,临近岁末。
林惊枝所住的偏僻小院难得多了几分热闹,因为要裁制新年的新衣,她就算是庶出不得宠的姑娘,但总归也是府上的主子,自然有府中负责针线的婆子过来测量她衣裳的尺寸。
料子是府里其他姑娘挑剩下的,裁制衣裳的婆子也并不是那些手艺顶顶好的,好在这些年里林惊枝不争不抢,除了晨昏定省偶尔露个脸外,她平常又穿得素净,在府中就像是个透明人一样。
“姑娘若有什么喜好尽管提出,奴婢会按着姑娘喜欢的样式去改进。”婆子收了手里握着的裁衣尺,像是说场面话一样,朝林惊枝笑着问道。
冬日昼短夜长,外头天色早已擦黑,林惊枝蜷着双膝靠坐在宽大的椅子上,身上盖了个厚厚的羊绒厚毯,她闻言朝婆子微挑起眉梢,脸上笑容美得像烛光下突然绽放的娇花:“妈妈按照你觉得不错的样式裁制就行,我并无什么喜好。”
她一截羊脂玉似的脖颈隐约露在冬衣外头,巴掌大的小脸上还带着些许婴儿肥,但无论是身段还是五官,浑身上下都精致得无可挑剔,已隐隐可窥见日后必将倾国倾城的美貌。
裁制衣裳的婆子小心抬眸看了林惊枝一眼,不想对上她笑盈盈的眼神,霎时一惊,背脊泛出冷汗来。
这些年,府中一直在传言,这位不得宠的六姑娘,恐怕会被豫章侯府的长辈想法子送出去攀附河东郡的权贵,好在不争不抢是个听话的,倒不像府里那些冒尖出头的庶女,因为得罪豫章侯夫人被随随便便给嫁了。
等裁制衣裳的婆子一走,前一刻还弯眉笑着站在林惊枝身旁的晴山顿时垮下脸来。
她朝婆子离去的方向冷哼一声:“布料是最次的,来的时辰也是最晚的,今日耽误了姑娘的晚膳不说,这会子再去大厨房,估计连热水都没有了。”
林惊枝无所谓慢悠悠伸了一个懒腰,纤长眼睫颤了颤朝窗子外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看去。
果不其然下一刻,一个提着食盒的清冽深夜从暗夜中走出。
他一身玄色冬衣,肩上还落着白雪,霜白的指尖握着食盒朝林惊枝走进,漆眸如墨带着晦暗不明的神色:“怎么知道是我来了?”
林惊枝皱了皱鼻子,抬手朝裴砚指了指:“闻到味儿了。”
这几年里,晴山早就习惯了两人的相处,她见裴砚从外间进来,当即悄无声息退了出去。
林惊枝娇软的身子蜷缩在宽大的交椅上,她也不动,理所当然往毯子里缩了缩。
裴砚走上前,从食盒里拿了碗筷,又摆好膳食,俯下身把她连人带着羊绒厚毯一起抱了起来,轻轻放到八仙桌前的绣凳上。
“先吃点东西。”
“别饿久了,伤了脾胃。”裴砚声音温和,动作小心又克制。
他从她七岁时找到她,用了将近八年时间,一点点接近她,到如今她对他全身心的信任和依赖,在无数个不眠的日夜里,他就像沙漠中枯竭求水的囚徒,她每一次的欢喜和信任,让他胸膛内那颗干枯碎裂的心,渐渐有了生机。
林惊枝接过裴砚亲手递给她的乳鸽汤,小口小口喝着,等喝了小半碗身上渐渐有了热气后,她放下碗筷,雪白指尖忽然握着裴砚宽大袖摆。
“你是不是又受伤了?”她看着他,那双透着几分忧心的眸子,软得令裴砚心颤。
他想摇头否认,可她指尖已经抚摸上他肩胛骨的位置,那里在昨日清晨中了一箭,虽然已经包扎上了金疮药但已经能看出包扎的地方,隐约同别处不同。
“不是很严重,已经上了药,过些时日就好了。”
“我不在的这两个月,你在府中可有被欺负?”裴砚稍稍往后退了些,避开林惊枝柔软的指尖。
他带着曾经的记忆,她如今还小又没长辈在身旁教导那些事情,这几年又被他护着,她对他依赖,他却不敢过于亲密怕吓着她。
林惊枝见裴砚往身后避开半步,她眼中有极小的失落一闪而过,粉润娇红的唇抿了抿,许久才道:“我除了晨昏定省,寻常都不出院子。”
“你安排在院中的丫鬟青梅和外院伺候的小厮云暮都在暗中护着我,也没有谁能真正欺负我。”
“只是……”林惊枝手中握着帕子,紧紧攥着,双颊泛出一抹薄红。
她鼓起了全部的勇气抬眸看着裴砚:“我听府中丫鬟说,男子及冠前该早就定下婚事了。”
“你日后娶妻吗?”
“娶妻后还会像当初说的那样一辈子护着我吗?”
林惊枝被裴砚护着的这几年,早就被他宠出了脾性来,胆子也极大,平日瞧见的事物读的书籍都是裴砚精挑细选出来的。
受了委屈有人暗中给她出气,三餐都是厨子精心调制再由人悄悄送到府中,有时他还会想法子让她假装生病,然后带她出府小半月。
她去过与河东郡隔着乌依江的月氏,登过极高的雪山,在夏夜里他带着她去松林骑马,冬日去温泉庄子小住。
&n-->>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