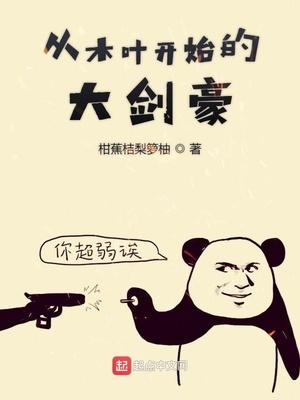52格格党>首辅宠妻手札 > 第73章(第1页)
第73章(第1页)
李鹤珣从始至终不曾言语,静静的看着他二人如同生离死别一般的对望。
唯有离他最近的归言瞧得见他几乎快要将指骨捏碎的,藏在袖笼中半遮半掩的手。
宁长愠步步靠近,直至停在他跟前。
二人皆是身长玉立,容色卓绝之人,李鹤珣冷静的看着他,听他道:“李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李鹤珣越过他的肩头看向坐在他身后把玩着暖玉的沈观衣。
沈观衣对上他看来的目光,眨了眨眼,模样无辜懵懂,大有装乖之意。
“好。”-
茶坊后院之中,宁长愠脚步滞住,回身看他,“李大人,日后娓娓便要你多费心了。”
李鹤珣缓缓道:“宁世子有时间关心别人的妻子,不若担心一下侯爷。”
“我父亲那儿我自有打算,这些年我虽不学无术了些,但他所犯下的罪该是何处置,我心里清楚。”
宁长愠继续道:“我找李大人借一步说话只是想提醒李大人,娓娓虽有身孕,但这并不表示她有多喜欢你。”
李鹤珣面不改色道:“她待我如何,我心中清楚,便不劳世子担心了。”
“是吗?”宁长愠轻笑道:“我只是好心,你倒不必对我这般疏离,今日我已经知晓我与娓娓再无可能,便是痴缠,以她的性子,至多落得个两败俱伤的结果。况且,我能留在上京的时日不多了,所以想告诉李大人……”
“关于她从前的……所有事。”
李鹤珣眸中闪过一道暗光,宁长愠没有旁的心思,他只是觉着,若这世上当真能有人捂热她的那颗心,恐怕也只有李鹤珣了。
他瞧得出来,娓娓待他是不同的,虽不知那喜欢有几分,或许很浅,浅到她自己都不曾注意,但旁观者清,他比谁都了解她,怎会发现不了。
“她的事我自会问她,大可不必从世子的口中知道。”
那样从容不迫,冷静自持,宁长愠原本生出的那一丁点善意顿时断了,“大人恐怕不知,娓娓性子强势,向来喜欢对她伏低做小的男子,越卑躬屈膝,越能讨她欢心。”
李鹤珣懒得再听他那些胡话,“世子若无旁的事,本官便先走一步。”
在他转身之后,宁长愠继续道:“她冬日畏寒,脾性比平日更加易怒,你大可以不信我的话,但若吃了苦头,可别怪我没提醒你。”
李鹤珣脚步不停,俨然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
宁长愠望着他离开的背影,掩去眼底的落寞,朝着皇宫的方向而去。
他方才的话半真半假,既李鹤珣那般清高冷傲,那便让他在娓娓那儿多吃些苦头,便是最终也不能让娓娓上心,也是他自己没本事-
沈观衣随着李鹤珣从茶坊出来时,天色尚早,她摸着手中温热的暖玉,有些沉甸甸的,但却暖和的令人爱不释手,她一变把玩一边好奇道:“你怎的突然来了?”
李鹤珣的目光悄无声息的从沈观衣手中握着的暖玉上扫过,“听归言说,你今日在沈府的事并不顺利。”
提起沈府,沈观衣便想要那个为了沈书戎去送死的女人,十分头疼,“随她去就是,她既想陪人下黄泉,我如何拦得住。”
李鹤珣在沈观衣上马车之时,默不作声的替沈观衣将暖玉接过来,“这两日京中事多,三府罪名已下,太子也被关入宗人府凶多吉少,大事频发,定会生乱,你若是无事,莫要出府。”
沈观衣心不在焉的嗯了一声,脑海中回荡的都是云姨娘将她救出来之时,脸上的庆幸。
少时在沈府,云姨娘便是在她娘死的前几日才被沈书戎接回来的,算起来,她不是那些冷眼旁观还要踩上两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