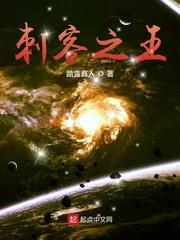52格格党>系统黑化想独占我[快穿] > 和医生恋爱(第2页)
和医生恋爱(第2页)
轻轻活动了一下垂在身侧的手指,他抬眸,所有在“温和平静”两个词之外的神情全部被收束起来,仿佛从来没有在脸上出现过。
景梵抬脚跟着走过去。
“坐下来吧,只是聊一聊。”
这位严医生的声音很温柔,令人如沐春风。钟虞点头“嗯”了一声,坐回了躺椅上。
“气色看上去很不错,看样子这几天睡得很好?”
对方语调轻快,钟虞不自觉笑了笑,“是睡得不错。”
夜晚浑身放松躺在床上睡觉的时候,是唯一能让她短暂“忘记”失明感受的时间段,所以钟虞反而比较放松。
聊天渐入佳境。
整个过程告一段落后,钟虞是被景梵倒完红茶后将茶壶放回桌上的动静弄的回过神的。
她这才发现自己无意识地转头朝着窗外陷入了沉思。
严怀引导着她,不知不觉把问题深入到了有关车祸的事。
车祸中“她”和双亲都受了伤,她昏迷失去意识的期间后者就已经被宣布死亡了,所以当她从手术的麻醉中清醒时,迎接的就是失明与父母死讯的双重打击。
阻碍复明的诱因很简单,但是想要放下却没办法一蹴而就。钟虞在经过刚才和残存记忆短暂的“共情”之后,明白复明的事可能心急也没用了,着急大概还会有反效果。
“任何康复的事都不需要操之过急,把它当成身体自然变化的规律,就像感冒的症状从开始到结束一样,无论如何都会经历一个周期。”严怀声音里带着笑意,“我已经能感觉到你的变化了。”
钟虞看不见对方的神情,但是却在最后那句话里听出了一些意味深长。
我已经能感觉到你的变化了?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的?不就是一句医生对病人的宽慰吗。
这念头只在她脑海里短暂地停留了一下。
“小姐,已经聊了很久了,需不需要吃一点茶点?”淡淡的嗓音忽然打破这种恍若只有医生与病人的单独氛围。
钟虞一怔,“已经过了很久了吗?现在几点?”
“现在是下午四点。”
竟然聊了一个多小时。她觉得有点口渴,手下意识伸出去想端起面前矮几上的茶杯,指尖刚触到冰凉的杯壁,手就被人轻轻握住了。
钟虞一愣,手下意识往后退了退。
“是我。”管家先生的声音在身边响起,她揣测对方一定是躬着身或者蹲了下来。
她没再把手缩回来。
“茶有点凉了,我帮您重新换一杯。”
“好。”
这个动作很小很细微,但是却隐隐透露出一种信息。
严怀不动声色地将一切收入眼底。
明明差点缩回手,但一听见是管家就任凭自己的手被对方握着了——看得出来这位钟小姐对她的管家非常信任和依赖,而这位管家也在有意识地用这种方式表现出这一点。
严怀抬眼装作不经意地打量这位管家,对方正垂眸用手指贴着杯沿试着杯内红茶的温度,仿佛这里只有他们一主一仆,而自己根本不存在。
看上去是一条忠心护主的狗。严怀微微一笑,但他清楚,对方实则是一头野心勃勃的狼。
“严医生,想再来杯茶吗?”钟虞收回来的手搭在膝盖上。
“不用了,谢谢。”
鼻尖忽然萦绕着浓郁的黄油和奶油的香气,钟虞知道是景梵把茶点端来了。她在这个空档继续和严怀闲聊,“严医生,是不是精神科的医生都很擅长让人放下戒备?”
“当然不,因人而异。不管是对医生来说,还是病人。有些医生缺少让病人信任的亲和力和方法,有些病人则对医生格外戒备,另外一些则很信赖与配合。”
顿了顿,严怀又说:“而你属于后者。医生大概是个很能让你安心、很有好感的角色,或许,你有熟识的人从事这个职业,又或者,你和医生谈过恋爱?如果和医生谈过恋爱的话,一定很难忘吧?”
钟虞眉梢动了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