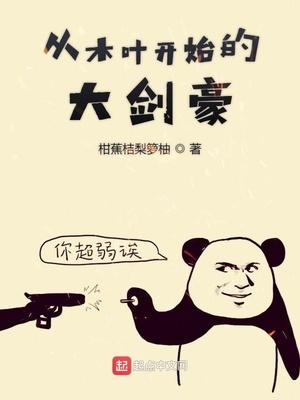52格格党>嫁莺娇 > 第四十六章(第5页)
第四十六章(第5页)
沈随砚转个身,看向前面,没有面对宁司朔,淡声道:“有何好怕,做了亏心事的人才会怕。”
宁司朔点头,“如此说来倒是我不如王爷看的透彻。”
话说出口后,两人间一时无话。
宁司朔见他久久不开口,便问他一句,“王爷在看什么?”
沈随砚语气还是一副平淡的样子,但是仍是染上几分的笑意,语气都变得柔和许多,“宫中的花匠向来都是最好的,我在想,若是萤萤宫中到了秋日还有如此多的花,定然会开怀。”
宁司朔的双拳攥紧,死死盯住沈随砚。
可是说出的话语却仍旧没有丝毫的改变,“是了,萤萤是爱花的,从前她总是喜爱桂花,我就着人为她寻了最名贵的品种栽在她的府上。”
说着宁司朔还恍然大悟一样,“就是如今丞相府的那一棵,那处的院子还是叫桂花院呢,是萤萤亲自取得名字,就算是冬日,也可以经久不衰。”
沈随砚有一瞬没有接话,狭长黑眸中尽显厉色。
藏在袖中的手渐渐攥紧,可话的语调却没有丝毫的改变,“萤萤同我说,早些年的时候,她没有玩伴,是宁公子陪着她,她也只将你当作兄长,其实送什么花,如此还留着并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收花的人知不知晓这份心意。”
说着,沈随砚咳嗽两声,“我身体不适,不能吹风,若是吹的太久,只怕萤萤回去又要着急。”
朝前走两步,他这才又顿下脚步,“还未恭喜宁公子,从洛阳偏僻之地回来,就重新又到殿前指挥使的公务上,如此殊荣,其他多少人都是不曾有的。”
宁司朔听见他说的话,倒是也不恼怒,“圣上厚爱,难以推拒。”
见沈随砚要走,他转身说上一句,“母亲前些日子还同我问起萤萤来,说若是她近些时日还是不开心,正好趁我上任前瞧瞧萤萤想要些什么,不如王爷回头帮我问我萤萤,不然我只怕私下去见萤萤不大好。”
沈随砚说的十分淡然,“无碍,萤萤只将宁公子当作兄长,我也是这般想的,宁公子若是想同萤萤见面,倒是无妨。”
宁司朔笑着说:“如此甚好。”
沈随砚先一步离去,等到走时,浑身的戾气是怎得都压不住的。
天上月亮高洁亮丽,可不是谁都可以染指的。
沈随砚在外头待了好一会儿,身上都尽数凉透才回到宴席之上,不想里头已经吵了起来。
“陛下,江浙水患来的蹊跷,三皇子竟在这时回了上京,说是要同陛下请罪,可是要置封地的百姓于何等境地啊,依老臣看,三皇子此时归京只怕别有用心。”
“你莫要在那处胡说,谁不知三皇子最是同天下百姓同甘共苦之人,三皇子已经派人去处理水患,此次回上京,也是在察看沿途百姓究竟如何,看怎样安置他们,才不是你说的这般模样。”
“如若当真如此,可怎么还是有如此多的流民涌入上京,上京如今的街道都变成什么样了,况且水患在此时发生,我看就是天降不祥之兆,定是谁人惹怒上苍,才会如此。”
堂上一时间炒的厉害,南谨帝听着用手支着头不发一言。
就在各位大臣都吵得不可开交时,他猛然间拍着桌子,“够了。”
说着厅中的人尽数跪下,沈随砚也垂下头,神色不明。
南谨帝一边拍着桌子一边道:“今日让众位爱卿前来,不是为谁的过错而无端的争执,是想要一个解决的办法啊,如今江浙一带的百姓多是流民失所,如若还想不出个办法来,才是真正的要完啊。”
最开始开口的那位大臣来,“方才顾大人说三皇子此次回京是一路在想解决的办法,正巧今日三皇子也在,不如我们听听三皇子如何说。”
南谨帝轻飘飘看了三皇子一眼,“齐王,你说。”
三皇子赶忙跪下,磕头请罪,“是儿臣治理疏忽,一路上以来,倒是还未曾想到什么好的办法,只是此事事出有因,书信之中恐怕说得不清楚,毕竟是在儿臣的封地,儿臣定然是要说明白的。”
南谨帝静默看着他两秒,随后抬手,“想说什么就说吧。”
三皇子又磕一个头,随后直起身子,不卑不亢道:“儿臣一开始知晓闹了水患,就已经去最先发现的地方看过。”
“江浙一带冬日将水排干,种下其他的作物,这水是引入沟渠之中的,再由沟渠统一汇入溪流中,最后随着水流一道向下,每家每户都是有固定的时间,若是一个村子与另一个村子之间恰好在一起,沟渠不堪重负,就会像四处蔓延,蔓延到旁边村子的田中,他们就也只顾着将水给排出去,如此一来,极其容易引发水患。”
“儿臣去问过最开始出现此种情况的村子,只是村子早已经被巨大的水流给冲垮,所有的人都如同一夜之间消失不见,其他上游村子的百姓也是如此;如若当真是天灾,又怎会出现这般巧好的事情,只是儿臣无能无力,虽知晓应当是有人在背后搞鬼,却无法找出真凶,还请父皇降罪。”
南谨帝沉冷的看着三皇子,三皇子说的每一句话都如同在对他道:有人不想他的天下太平,是觊觎他的皇位了。
他冷笑道:“好,好啊,既然如此,那就先派三千人马去江南,宁司朔。”
宁司朔很快站出,“臣在。”
南谨帝满意的对他点头,“三千人马由你来带,明日就出发,若是查出什么来,回来,朕重重有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