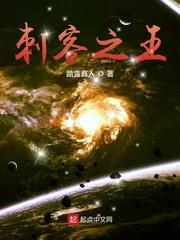52格格党>孤王有病 > 046(第4页)
046(第4页)
蹙眉深思,对了,他方才用了“陛下”、“臣”……
真珠打了个冷战,手臂冒出一片鸡皮疙瘩。
她张了张嘴,半晌才挤出一个“好”字。
陆呈雪表情轻快,好似了了一桩心事,临走时,他在门前停下步子,有些犹豫地说道:“殿下真心待陛下,有人只怕是要眼红呢。”
真珠只觉莫名,反应过来后,匆忙收好帛书赶回长极殿。
兰重益刚从春台回来,她把这件看似古怪又诡异的事细细地讲给他听。
伏在案前的兰重益连头也未抬起,“若王师曾将他归于不可深交来往的名册里,那也不足为奇了。陆呈雪做到少府之位也不全是蒙受祖荫,他如今怕是意识到了什么,真心要助陛下一臂之力。”
他提笔蘸墨,“他心不在仕途,主动提出实属难得。陛下不是要淬炼兵刃,于公于私,都可放心用他。”
练字是兰重益多年养成的习惯,能保持这种习惯的人大多很有耐性。
真珠坐过去,兰重益在敞亮的窗下写字,行笔从容,笔势飞动,书风劲稳放纵。
常言道:字如其人。字里行间便能看出下笔者的心境旷远。
兰重益诸体皆会,造诣颇高,真珠都知道,她看过他早期的书法,比起如今多几分随意飘逸,大概是身心局限的缘故吧。
真珠不再打扰他,展开帛书研读起来。
韩康这个人和窦明辨大有不同。
窦明辨太耿直顽固,认定一条道就会走到底,韩康稍显圆滑,更懂变通,不忌讳为达目的使用手段阴谋。
他在书中说:“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
氏族犯了法,必须狠下手惩办,不可放任贵族。这点庞嫣在临江已经做到,只是效果不甚明显。
他又说到朝廷的几大奸邪,如蔡熹之流,是国家痈疽,不斩草除根必定渗透内部,要根除必须累积或罗织罪证。
庞嫣要借助蔡熹的势力,必然维护他,此事难上加难。
这些事情看似很好处理,但一件件施行起来谈何容易。
没有夜朝不用坐殿,真珠本想趁此和兰重益商议一二,转念一想,事情繁多,捋也捋不出头绪,反而不知道如何开口。
她烦恼地叹息,对着梳妆镜懒拆发髻。
“哎呀!”她忽然叫了一声,连忙捂住嘴,从镜中望着满颈子的红点有些傻眼了。
难怪陆呈雪说“眼红”那样莫名其妙的话,她丢人都丢到朝上去了。
兰重益掷下笔,进来问:“是不是伤口不舒服?”
“公子怎能这样啊,让我还怎么去见人。”真珠气恼极了指着脖子给他看。
兰重益抬起指尖,摩挲那些红点,面颊染上微粉,“以后我会注意。”
她把领子拉高,气冲冲地往外面走,“没有下次,今晚我自己睡,公子去别的殿就寝吧。”
“真的吗?那夜里我叫人把门窗锁紧,免得小猫又钻进来。”
兰重益说笑着,也不生气,任她去了。
当天夜里,真珠很没骨气地翻了兰王的寝宫,做了回小野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