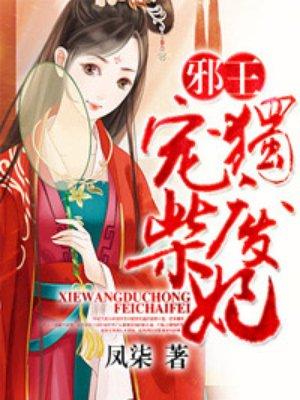52格格党>春棠欲醉 > 第286章(第1页)
第286章(第1页)
書房猶在眼前,緊闔的槅扇木門近在咫尺,內里的昏暗似重重黑影。
宋令枝下意識想要逃離,她語無倫次:「我、我可以自己回去的。」
沈硯垂眸,似笑非笑:「不是走不動了?」
宋令枝磕磕絆絆:「我、我可以尋大夫來……」
話猶未了,她仍已經被抱著進了書房。
臨窗炕上多出兩抹交疊身影,鶴氅仍攏在肩上,擋住了氅衣之下的動靜。
宋令枝腳腕纖細單薄,輕而易舉讓沈硯握在掌中。
書房暗香疏影,滿室幽香瀰漫。
青玉扳指沁涼,貼在自己小腿處。
緩緩往上。
宋令枝手臂環著沈硯的脖頸,少頃,一雙杏眸水霧瀲灩,泛著盈盈水光。
一窗之隔,岳栩雷厲風行的身影出現在門外:「主子。」
沈硯淡聲:「——說。」
岳栩抬腳進屋的動作頓住,聽出沈硯話中的冷冽,他不敢隱瞞,一五一十將福安堂搜出的帳本上報。
腦袋低垂,岳栩目光牢牢盯著自己腳尖。
金吾衛辦事向來果斷迅速,只是這回的事本不需要金吾衛親自出面的。
料理一個小小的福安堂堂主,一個江南知府就夠了,犯不著暴露他們身在江南之事。
只是一想起當時在福安堂門口之事,岳栩忽然不寒而慄。
練武之人耳力向來是極好的。
宋令枝那一句「狀元郎曾經是我夫婿」,岳栩聽見了,沈硯自然也聽見了。
岳栩如今還記得,月白色鶴氅之下籠著的身影頎長,沈硯只是淡淡抬眸,漫不經心朝馬車外的岳栩投去一眼。
岳栩當即遍身生寒,落在臉上的目光如寒刃銳利,森寒徹骨。
怕是岳栩晚踏入福安堂半步,沈硯會忍不住親自了結。
「主子,福安堂另外兩位副堂主也已經招供,往外受賄的名單也在堂主的屋中找著。還有先前那罰跪在祠堂的孩子只是受了皮外傷,並無大礙。」
岳栩渾厚嗓音透過紗屜子,清楚落在宋令枝耳旁。
貝齒緊緊咬著紅唇,隱約有血絲滲出。
二人鶴氅未解,沈硯面不改色低垂著眼眸,眼中眸色沉了幾分。
青煙燃盡。
宋令枝禁受不住,又怕溢出的聲響驚擾到窗外的人,她眼中含淚,一口咬在沈硯脖頸。
齒痕深深烙印在沈硯肩頸,他挑眉,好整以暇望著宋令枝。
眼中掠過幾分不易察覺的饜足之色。
窗外。
岳栩拱手站在冷風之中,只覺沈硯的回話一次比一次遲:「主子,還有明枝宮一事……」
屋內好像有什麼東西被打翻,青花瓷瓶碎了一地。
岳栩一驚:「——主子!」
沈硯嗓音慵懶:「傳水。」
岳栩瞳孔驟緊,後知後覺書房還有人在。思及沈硯先前在福安堂前的厲色,岳栩再不敢耽擱,匆忙告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