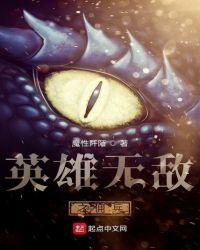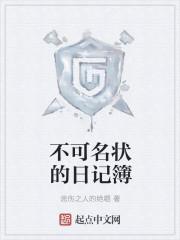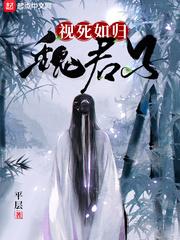52格格党>朕真的不务正业 > 第824章 悯畸零幼主识民疾 破陈规能臣立新章(第1页)
第824章 悯畸零幼主识民疾 破陈规能臣立新章(第1页)
第824章悯畸零幼主识民疾破陈规能臣立新章
又是一年春来到,有人欢喜有人悲,赵南星觉得自己是最悲伤的人,而大明皇帝很清楚,赵南星一点都不可悲。
他回到江南,他被宁远侯揍了这件事,可能还是他的谈资、是他继续和江南势要豪右讨价还价的筹码。
毕竟被揍过,也是一种不被权威所喜爱的认证和标签,会受到一定的追捧。
有人问价的时候,他可以骄傲的说:我被宁远侯揍过!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只要赵南星足够的无耻,这也是他的卖点之一,只要他作为读书人,有这种无耻,就可以变现。
这士大夫所标榜的的道德,往往跟青楼里娼妓对外说自己卖艺不卖身,没什么区别,不卖身,大抵是价格没谈拢,价格谈拢,士大夫也可以出卖道德,把挨揍的事儿,翻来覆去的讲。
多少贱儒,受一点点委屈,就能念叨一辈子。
即便是地方衙门畏惧皇帝圣意,不准赵南星继续聚谈讲学,他一个举人,有一定的免赋税的资格,只要挂靠诡寄田亩,也能过上富家翁的生活。
真正可悲的是养济院这里的畸零户,因为天生残缺,进了养济院也没人会领养,而且养济院条件有点差,生病后,也没人会照顾,更没有汤药,很多病,只要一碗热水就足够了,但一碗热水也是没有。
甚至因为养济院孩子的欺凌,吃不到饭,身体越来越差,最后死在无人问津的角落里。
即便是在养济院里,大多数的畸零孩子,都长不到成年。
朱翊钧过年前,都会到养济院来看看,东西舍饭寺和养济院,有大量的官舍,一到冬天,就有人投奔过冬,算是封建帝制封建统治下,少有的温情。
皇帝、皇后、太子亲自探望,算是朱元璋的祖宗成法,当年朱元璋在各府州县办养济院的想法,其实也简单,穷民苦力走投无路的时候,有个投奔的去处,就不会揭竿而起,掀翻他老朱家的江山了。
养济院的官舍是有限的,而且所有用度都靠捐赠,再加上有些道德败坏的家伙,从中贪墨,各地的养济院逐渐成了藏污纳垢之所,捐赠来的钱粮,多数也给不到这些孩子身上。
朱翊钧讲祖宗成法,他每年过来一趟,不敢说能让养济院彻彻底底的干干净净,但总能干净一些,至少他来的时候,这些畸形的孩子,不健康的孩子,过年能吃上一口肉。
有些势要豪右为了讨皇帝欢心,或者为了表忠心,皇帝来的前一天,会捐一些钱粮,让皇帝看到他们家是积善之家,比如西土城的姚家,北土城的米家,每年都会捐一大笔钱粮,大约有两千银左右。
作为榜一大哥,朱翊钧每年都能看到他们捐赠的钱粮。
朱翊钧很清楚,他这十五年做的事,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
既没有让大明走出王朝周期律的困境,也没有改天换地,天下还是那个封建帝制的天下,就是在原来的框架上,修修补补,让大明能够继续维持下去。
“爹,我和他都是人,没什么不同。”
“我习武之后,吃饭也是这样狼吞虎咽,娘亲和奶奶都教训我,说我没有礼数,但我饿,他也饿。”朱常治忽然伸手指着一个狼吞虎咽吃饭的孩子,说了一段让朱翊钧十分惊讶的话!
朱常治指的孩子,大概只有八岁,面相十分的凶狠,少了一只眼睛,看起来更加恐怖,但他很瘦弱,看得出他在养济院的境遇不大好,大概是被排挤的那一类人。
孩子的世界,也不完全是斗狠争胜,还有拉帮结派,他这种凶狠,又不听话的孩子,朋友自然很少。
朱常治习武之后吃饭太快被教训,李太后隔代亲,王夭灼是心疼,最后都没管得住,不了了之,随朱常治去了。
大明礼法对皇子进食,有着非常明确的规定,不仅仅视为个人失仪,更被看作是对社会秩序的潜在威胁。
《礼记·曲礼上》明确规定:毋抟饭,毋放饭,毋流歠,毋咤食,毋啮骨,就是吃饭不要捏饭团、不要把吃过的饭再放回盛饭的器皿中、不要流口水大口吞咽、不得出声响、不要啃咬骨头出声响,否则就是失仪。
《童子仪》明确规定:饮食必执匙箸以正,不露暴殄之相。
李太后也曾经多次纠正过朱翊钧的仪态,但李太后从没纠正过朱翊镠吃饭失仪,在李太后看来,皇帝就该注重礼仪,潞王注重反而乱了纲常。
吃饭的礼仪逐渐演化成了对社会秩序的威胁,是在朱熹之后,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特别指出:所以养德性,非徒养口体也。
就是说吃饭饮食的,应以礼仪为先,可以养德,而非满足口腹之欲。
自此以后,吃饭的礼仪,就跟德行有关了。
朱翊钧伸出手,摸了摸朱常治的脑袋,郑重的说道:“治儿啊,你要记得你说的这句话,知道吗?”
“嗯。”朱常治用力的点了点头,不知道父亲为何如此郑重,但他知道,这是他自己看到的,想到的,他会一直牢牢记住。
朱翊钧笑着问道:“治儿啊,让他给你当陪练如何?和勋卫子弟一起进宫出宫,住在官舍里,他虽然少了一只眼睛,但你把他从养济院里救出来,他日后会为你拼命的。”
“像骆叔那样?”朱常治思考了一下,想起了骆思恭,人高马大的骆思恭是皇帝的最后倚仗,现在在全楚会馆全权负责张居正的安全。
朱翊钧点头又叮嘱道:“嗯,以后在外面不要叫叔叔,要不然那些言官,又要揪着不放了。”
对于肯用命来保护父亲的骆思恭,朱常治非常尊重,但在外面他会顾及君臣,不会这么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