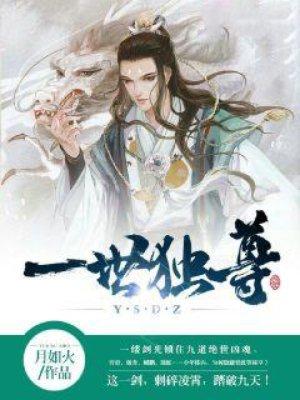52格格党>爱在沉梦初醒时/爱在沉梦初醒时[无限] > 第254章(第1页)
第254章(第1页)
电梯的地面淌着一滩血,门再次关上了。郁臻形单影只,在走廊轻悄前行。他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监视他,倘若现在再来一个枪手,他也会加入“生死有命”的行列。不过他终究是相安无事地走过了20米。这条路的尽头是另一条横向走廊,排列着六个房间,无楼梯或明显的出口,郁臻一时间不知往哪儿去,他心情麻木,不做选择题了。杜彧:“去中间的,里面有东西。”——你透视眼吗?门关着你都知道里面有东西。杜彧:“我听到了。”——那你听得见安全出口在哪儿不?杜彧:“应该在哪一扇门后。”——废话。郁臻将信将疑地推开了中间房间的门,里面灯光暗暧,布局拥挤狭促,因东西堆积过满,带给人铺天盖地的压抑感。不是游戏场所了,更像一间储藏室。爬行动物和啮齿动物的腥臭味混合着旧报纸发霉的潮味扑面而来,郁臻掩鼻走进去,不敢关门。房间面积不小,四面贴墙立着尺寸相同的合金置物架,架子上层层叠叠的摆着大型玻璃缸,他凑近一瞧,底部黑压压的全是蛇。一口缸养十多条,各花色的无毒蛇们蜷缩或拉长身体,在缸底缓慢地扬头扭动着,凉滑的鳞片紧贴玻璃,蛇身交缠时背鳞泛出冷艳的光。郁臻不怕蛇,仍然不由得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置物架的最底层是铁笼子,整个房间的噪音都源于它们,成群结队、叽叽喳喳的小白鼠。显然是养来喂蛇的。这些爬缸和鼠笼打扫的频率不低,但安置得过于密集,那股气味熏得郁臻想流泪。杜彧:“这个养殖规模不小,应该不是个人兴趣或观赏物。”——养来吃蛇肉?杜彧:“如果不是开餐馆,照这个量和吃法,那一家人早就被寄生虫感染身亡了。”——哪一家人?杜彧:“那边的桌子上放了照片。”原来正对房门的那排架子后留出了几平米的小空间,郁臻绕到那后面,脚步一顿。墙上贴了无以计数的旧纸张,其文字内容包括但不限于新闻、社会评论、案件分析、照片,以及复印的书页和打印的影像资料……宛如墙纸一样严实地遮盖了整面墙。墙边的一张桌子堆积了如山高的书本,笔墨杂乱摆放,一幅相框搁在桌角,谁轻轻一碰,它便会坠地摔碎。郁臻先拿起了相片,那是一张完整有脸的全家福,11个人,站最前面的女孩是更小一些的司雅,她编了两条麻花辫,脸颊圆润饱满,笑容甜得宛如水蜜桃。这张照片的拍摄时期比杜彧拿到的那张更早,每位家庭成员都笑得开心、满足;这是与亲人关系和睦,生活富足的人脸上才会露出的表情。这一家人看起来着实不具备变态反社会的素养……全家福上,看面相年龄和司雅是同辈的男性有四个,两名青年,一名少年,一个小男孩。但据蓝玉的回忆,司雅只说过自己有两个亲哥哥,一个亲弟弟;分别是:正常人大哥、让她害怕的恶魔、正常人弟弟。那多出来的一个同辈估计是她的表哥或堂哥?不,是小叔叔也说不定。首先弟弟最好认,是贴在司雅身边的小男孩;但三位兄长挺让人犯难,两名青年的相貌平平,不容易分辨血缘,仅那名年纪稍小的少年和司雅的长相有几分相似。长得像的肯定是亲生的,而这名少年的年纪不可能是长子……谁是大哥不重要!因为次子才是司雅所说的“恶魔”!郁臻快把照片盯穿了,难以置信,这恶魔长得太纯良了吧,看不出哪里有先天性残疾啊……杜彧:“不要以貌取人。”郁臻:我最奇怪的倒不是这个。之前你拿来的合影没有眼睛,我不敢百分百确定,现在看到完整的照片,我确定了,我们一路碰到的青蛙头、猎人,他们都不这张照片上。杜彧:“嗯,想杀我兔子头我摘了他面具,他也不在照片上。”郁臻:所以他们根本不是司雅的家人。杜彧:“那就是雇佣来的人。”郁臻:雇佣保安可以理解,但是上哪儿去雇佣一批不怕死还敢杀人的npc?他们是一个有分工和谋划的组织。我一开始猜想他们是司雅的亲人、想为她复仇,因为唯有血缘关系和宗教才能维系这种盲目疯狂的集体行为。可他们竟然不是血亲,那究竟是什么样的利益和动机在支配他们的行动?杜彧:“可能他们乐在其中,世界上有不少恶趣味的人,有时候并非为了利益,也许单纯是觉得好玩。”郁臻:等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