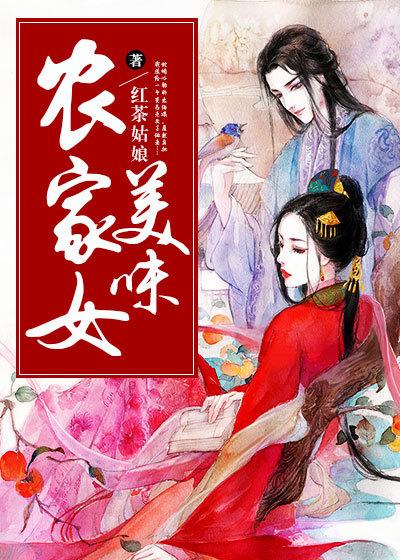52格格党>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 > 第406章(第1页)
第406章(第1页)
唇角凝了血,宋诀陵始终端着轻蔑的表情,任那老将如何的笑他,仍似胜者那般的清高。
伯策喘着粗气,冷笑道:“我当年几战你们魏的鼎西王李连,除却几回平手,那位皆败于我手,最后一战更是被我废去两腿!你这后生,想要与我平起平坐,着实天真!”
宋诀陵头一次张嘴回了他的话:“可是你的儿子布贡达死在了我的手上。”
那伯策也不知心是铁铸的还是怎么,闻言竟是眼也不眨,他说:“布贡达并不是你杀的,他没能完成长生天降下的使命,是受天罚而死!”
“是啊,我便是长生天的使臣,今儿我奉天旨,夺你性命——!”宋诀陵说罢,霍然欺身上压,叫剑锋近乎要触着那人的鼻尖。
伯策虎体熊腰,这会儿却被宋诀陵压制得动弹不得,他不知宋诀陵的暴起之力竟达如此,当即吃了一惊。
眼见宋诀陵的身后人马渐趋汇合,伯策咬碎牙终于脱身,他调转马头,忽而跑出兵营向北跑去。
宋诀陵驻步略微算计,此地仍为大漠,若要步入草地少说还要再向北连赶十日,而秦兵粮草短缺,为节省粮草,应是能省则省,十有八九不会选择在大漠中扎营。他只消在这片被白雪掩埋大半的黄沙中杀死伯策,以绝其汇合之路,便仍有胜算。
宋诀陵于是召了余下精锐,向北奔去。
燕绥淮的视线已叫敌军喷溅的鲜血糊作殷红,他猛力瞪着眼,强忍刺痛,抬头蓦见那前后两支逐渐叫沙风淹没的人马。
他痛苦地发出一声嘶吼,将面前刺来的长枪马刀一并推去,恨不能将犯边者一刹碎作肉沫。
唐刀被鲜血裹了一层又一层,仿若击石海浪那般乱掀跳珠。他赤红着一双眼,却唯有眼睁睁地瞧着宋诀陵的背影隐匿于茫茫大漠。
他在西,俞雪棠在东。
她不仅刀法了得,步兵列阵也很有巧思,打得这头那些个轻视女儿家的秦贼落花流水。可是秦兵如蚁,竟叫她杀也杀不尽。
宋诀陵的背影晃在远方,她空洞着一双眼,手臂麻木地向前挥刀,片晌才咬牙回过神来——
不能叫宋诀陵的辛苦白费!!!
她于是回身阵中,只叫后头那些个在铁盾之后潜藏已久的弓手斜身放箭。
唰唰啦啦,一时间马嘶人呼,一阵乱响。其间也有人不慎蹭着了吞没大半营帐的烈火,一刹变作这摧毁这十四年虚虚太平的冲天烟尘。
人肉的焦味如针一般被吸入心肺,扎得两军人马皆是痛苦不堪。
秦人拜天。
战啊,战啊,为了熬过此冬的食粮,为了其族的存留。
魏人嚼土。
战啊,战啊,为了不让疆土的操守,为了其国的永昌。
在被那些个攘权夺利的缱都官爷遗忘的北境,悉宋营厮杀不停。宋家军个个十指如草木,纵然被风暴卷去,仍以仅剩的,如草根扎进土壤般紧咬着刀剑,削劈砍刺剁。
鲜血染红了白雪黄沙,粘稠不肯下渗的鲜血,是代替了他们被碾碎的眼球,不肯瞑目的双眼。
后来,后来他们的血肉叫沙吃了,他们死了。可破碎的皮堆上还落有一个模糊宋字,与它们相生相灭。
戍边者成了梅,开在了北漠深处。
震州半月无雪,季徯秩率领的兵马行至城郊时,天上却又飘起了鹅毛。
他打一破败庙观前行过,心头一紧,又动了取根香来拜神的念头。然其于诸人修整之际进去走了遭,却只见了尘灰与蛛网。
空荡的庙观里头就连木梁也叫人偷去,他抚摸着那些个断裂的窗台,喃喃自语:“从前皇叔带我远游,曾领我来过此地,当年香火何其旺盛。供台几回漫火,如今怎就连烛台也不剩呢……”
原来越近繁华处,人越是贪。
季徯秩望着远方,眼一晃似乎跨过震州几城,径直望见了缱都高耸的城楼。
宁晁顺着他的视线看去,若有所思良久,终于问:“薛止道直接攻城,叫禁军半数覆没,为何没如徐大人与林大人所料那般不得民心呢?”
季徯秩挥手扫他肩上雪,说:“是因他二位低估了百姓对于魏帝的恨意啊……耽之和林大人算遍世事,他们能算得了大局,终究算不尽人心。——高坐云端上,哪可观清人间事?”
宁晁蹲身从麻袋里抓了把草料喂给霜月白,说:“可在下听闻那二位皆在平州烂沟摸滚许久,这样也可称作高居九天吗?”
“耽之和林大人,虽曾身处贱处,可他们心比天高。满眼皆是家国大义者,难能看清小家小情。他们站得太高了,高得他们眼里只剩了上位者。你说他俩纵然身处泥潭,看的亦是峰巅近处,怎么能不是高坐云端呢?改天者必高人,此乃徐林二人的自负之处。他们知晓百姓受苦,故而要换天,这是他们的因。可是百姓被魏家摧残已久,饱食尚不得,哪还能顾及改姓?”季徯秩叹道。
“那么如今常兄在震州边城里做的倒是很好!我们打那城而过时,在下见拥护他者多为庶民,可不得比那些欲|望颇盛的官爷诚心不少嘛!”宁晁交臂说。
“之安兄要民拥,等价便可;他要官拥,非用更重者相交换。”季徯秩蹭着腕子佛珠串,又说,“之安兄他呀,曾招惹震州恶霸史女婿,叫该州官给扣了个万万不能搭理的帽子。之安兄他力争民心,虽多是因着胸怀宽广,其间却也含了不少迫不得已。”
“所以说……时来运转,有些事,还真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季徯秩笑起来,“哎呀,我今儿怎么尽同你嚼这些虚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