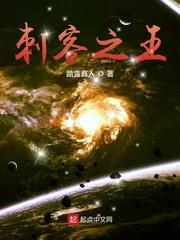52格格党>雪满楼 > 第16章 汉宫宴饮(第1页)
第16章 汉宫宴饮(第1页)
解玉一愣。
倒是从未有人这般称呼过她。
她回过神,身后之人缓缓而至,佩环叮咚,温润清朗,正是温衡与。
“解姑娘,”温衡与淡笑着,虽是询问,可看神情却像是早就认定了她是解玉,“久仰姑娘大名,今日冒昧打搅,还望姑娘莫要怪罪。”
解玉欠了欠身。
她与温衡与并不相识,可从他踏进店里的那一刻起便已猜到了他的身份。
京中的温姓公子,又这般光风霁月的人物,只有那位翰林学子温衡与了。
她看着温衡与:“不知公子所为何事?”
温衡与道:“听闻姑娘与家师乃是旧识,早就听闻姑娘喜好书画,藏画颇多,尤其那副汉宫宴饮图,在下垂慕已久,早前碍于一些缘由无法前去拜会,不知姑娘今日可有空闲,能与在下一叙?”
解玉不作声。
温衡与接着道:“在下知晓姑娘已是出阁之人,私下与外男相会是为不妥,只是若非在下执念太深,也不会这般突兀地叨扰姑娘。”
“如若姑娘心有顾虑,自可寻他人在旁,找一处敞亮地方,以免落人口实。”
解玉对这个温衡与倒是有些了解,他的老师是翰林大学士章流。
章流虽早已退出了朝堂,可门下桃李满座,朝中许多要职官员皆出自他的门下,因而地位颇高,又加上他为官期间清正廉明,淡泊名利,名声极佳。
唯一影响过口碑的事,便是两年前出入寻花楼一事。
须发尽白的老者身后只跟了一个书童,就那么光明正大地走进了寻花楼的正门,在里面待了足足两个时辰,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风波。
可自始至终,章流都未出言为自己辩驳,有人说他是心虚,无力自辩,不过更多的人则是觉得他出入寻花楼并非是为寻欢作乐,不肯反驳也只是清者自清,不愿作无谓的争辩罢了。
这风波没过多久就平息了,不过解玉倒是记得清楚,她记性极佳是一原因,更重要的缘故则是,这章流确实性子古怪,来了寻花楼不请姑娘不沾酒,只是与老鸨绾娘在房内待了两个时辰,便匆匆离去了。
章流走后,绾娘并未流露出何异常之处,楼里姑娘们虽好奇,可到底也不敢议论绾娘的是非,时间久了便也就将这件事放下了。
眼下温衡与蓦然提起章流,像是在提醒她什么似的,解玉沉吟片刻,却问道:“奴家与章老先生并未打过交道,尊师缘何会提起奴家?”
有一点温衡与说得没错,她确实喜爱书画,平日里也爱作画,这事儿不是什么秘密,绾娘和素日里想要讨她欢心的男人们时常会送些稀罕的画儿来给她。
他说的那幅汉宫宴饮图,她有些印象,只是叫他这么一问,倒多了几分原本没有的思量。
温衡与笑笑,只道:“解姑娘不必紧张,在下只不过是听家师提起过这画儿在姑娘处罢了,姑娘若是有不便,在下自可以另觅时机。”
解玉道:“……倒也并非不便,只是从前那些画儿,在我离开寻花楼时变卖的变卖,留下的留下,带走的带走,实在不记得那幅汉宫宴饮图现在何处了,待我回去仔细找找,再另给公子答复。”
言罢,她朝温衡与欠了欠身,“温公子,告辞。”
温衡与注视着她离去的背影,面上依旧是一派风轻云淡,波澜不惊。
倒是一直立在暗处的云升看着两人的身影心乱如麻,不肖片刻,便转身向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
解玉回到高府时,感觉到一直跟在身后的尾巴似乎消失了。
绘春还回忆着方才遇到温衡与时的情形,问道:“二夫人,您似乎还未告知温公子该如何联络呢。”
解玉淡笑着摇摇头,她这哪是忘了啊,她这是压根儿就没想着再与他打交道,“他这人心思重得很,还是少来往为妙。”
绘春一知半解,倒也没再说什么,跟着解玉一道进了院子。
解玉独自一人回了房,关好门窗。
即便是院子里的人多了,她还是不习惯有人时时刻刻候立在一旁,还不如叫她们多歇歇呢,一个个也都是半大的孩子。
“叩叩!”
门口忽然传来敲门声,绘春的声音有些急切:“二夫人,夫人找您过去一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