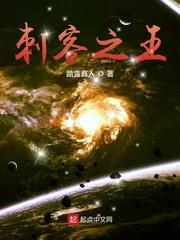52格格党>落花记 > 第20章(第1页)
第20章(第1页)
“直接问我不就好了。”他拉起孔姒的手,意识到被他刚才用力按红了,补偿地揉,“我的生日在春天,四月十日。”
还好没有错过,孔姒卸下压力。
“这么问,到日子就没惊喜了。”她的惊喜计划还没打开,已经被快进到大结局。
“你好好考试就是惊喜了。”齐烽满不在乎这些,牵着她往外走,“吃汤圆吧。”
书房门紧实地合上,砰地一声。
不止在此刻,后来她经过书房,门时常关着。除非齐烽坐在里面加班,孔姒才能蹭进去坐在他身上,他双手把她抱得很紧,几乎不让她往他手臂范围外走。
齐烽吻她说,害怕她跌下去。
古怪的是,仅从膝盖摔到地面,如此微不足道的距离,不值得他用险些粉身碎骨的语气。
齐烽避风港
花又开时,代表齐烽的生日近了。
北城市政爱种桃树和郁金香,散在日光下,耀动欣欣向荣的颜色。世界姹紫嫣红里,齐烽并未想起他即将到来的生日,偶然看见梨花树,缩在整排张扬的桃花后,像不肯见人的小姑娘,齐烽愕然想起确实是春天了。
他与孔姒的第一次见面,正在他生日的当天,在梨花的季节。这也许是他记忆的锚点,此后每一年,他生命的年轮增长一圈,梨花就多一片落在他心上。
生日当天齐烽还是忘了,他向来不重视这个日子。齐家父母起初会帮他庆生,那时齐烽还不了解自己的真实由来,和其他孩子一样虔诚地吹灭过几回蜡烛,闭上眼默默许愿,生怕漏出一点儿声音。
愿望说出来,就不灵了。
后来一朝撞破,齐烽才擦开那些雾蒙蒙,发现他的出生日没几分喜气,他的降临是无可奈何,生日后面无法再跟着“快乐”二字,于是他亲手关掉这些无用的仪式感,没有人再自讨无趣为他庆生。
每天八点推开卧室门,孔姒准是不在的。离高考仅剩两个月,她成日焦头烂额,脸色忙得像快枯萎,齐烽倒不好意思再消耗她的体力,顶多检查她是否按时吃饭。
令他意外的是,孔姒忙里偷闲记住了他的生日,还把准备好的礼物放在他卧室门口。齐烽一推开门,听见纸袋簌簌倒地的动静,轻飘飘地响,像他多年前吹灭蜡烛时咻的一声。
纸袋上贴着便利贴,很难免俗地写着“生日快乐”。
他把礼物拿出来看,一条藏蓝色领带,均匀织着细小的四芒星暗纹,在早晨八点的日光下莹莹闪动。
想到今日要见孔隅,齐烽选择把这条领带戴上,就当是他带着孔姒见证这一刻。
直到孔姒快成年的这一年,孔隅的父爱才又缓缓表露出来,也许是他意识到,这个年纪的夫妻不会再有孩子,孔姒是他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孔隅开始关心孔姒的未来。
孔隅特意空出时间,参加孔姒的百日誓师大会,这对他而言已经算重视,然而孔姒没有留位置给他,她把家长的位置留给齐烽。
人头攒动中,齐烽微微作势要站起来,“你来坐?”
“算了,我跟她打个照面就走。”孔隅摆摆手站着,等孔姒自己找过来。
齐烽心安理得占着家长位置,看见孔姒从人潮中挤出来,额头上系着“一鼓作气”的红布带,手捏着一根气球线,她刚笑意盈盈,嘴角忽地垮下去。
无论过多久,孔姒都不会再承孔隅的情。她拉起齐烽扭头就走,下意识与他十指紧扣,过分熟悉的身体没有安全距离和避嫌。
齐烽愣了片刻,回握住孔姒的手,目光斜觑被冷落的孔隅。
火一样的夕阳下,身为父亲的孔隅尚存几分敏感。他正看着齐烽和孔姒交缠的手,大抵是品出一丝不对劲,憋了一个多月,忍不住把齐烽约出来仔细聊聊。
花开得确实不错,齐烽坐在咖啡店靠窗处,盯着窗外看,其实他降临时的世界一直很美好。和暖的光对每一寸土地无微不至,不比盛夏热烈,晒得人睁不开眼。这样暖融融的温度,适合他心平气和对孔隅坦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