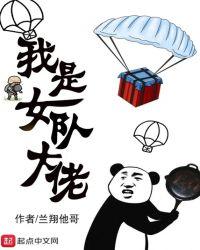52格格党>多伦多有条羊街 > 第210章(第1页)
第210章(第1页)
“对,昨天下午。”老太太笑叹,“十来年没坐过飞机了,差点把我这把老骨头颠散咯。”
兰珍笑笑:“那您这次是来办事的吗?”
老太太一双深邃的眸子却犀利地看过来,然后笑道:“苏小姐,我是专程来见你的呀。”
兰珍的笑一僵,心中略感不妙。
正不知如何接下文,负责他们这一桌的服务员救了她,是个香港阿叔,像很多档次不错的粤菜馆的服务员一样,他的衬衫领带熨烫得十分平整。他是来问问她们,要喝什么茶水?顺便撤走两副多余的餐具。
阿叔泡了茶来不久,一位阿嫂就推着点心推车过来了,一面把那一推车琳琅满目的小茶点展示给她们,一面吐出一串广东话。兰珍刚要问:“你会说国语吗?”
反应很快的阿嫂已经先她一步,无缝切换成了普通话:“要不要?我这里有哈搞(虾饺)、擦骚酥(叉烧酥)、藏(肠)粉”粤腔很重,说得倒是顺溜。
当然,让人家把“国语”讲得溜是有代价的,她们时不时就会过来给你推菜,你要是跟客人聊得入港,随口应一声,结账的时候,账单总是让人咋舌的。
阿叔阿嫂们一阵忙碌后,桌上多了一壶雨前龙井,还有几蒸屉几碟子的点心。
等他们都走开了,兰珍以为老太太会深入谈论一下,她为什么要大动干戈地来见自己。谁知阿嬷胃口不错地吃了好几块点心,和她扯了一堆北美几大都市的天气、中餐之类的闲话,并没回到方才的话上去。
兰珍放松了警惕,想:也许刚刚就是老人家开个玩笑而已,说是特地来看我,不过是让我显得特别而已。都怪自己最近有点神经过敏,听风就是雨的。
还好,老太太似乎还沉浸在自己的话题里,全然没看出她心里的小九九。
“你说是不是很有意思?”老太太笑道,“我从前住的都是暖和的地方:芜湖、重庆、上海、香港、台北,我都住过的。没成想,到了美国以后,我竟然在纽约住下来了,刚去的时候真嫌冷,这么多年,竟然也适应了,而且这是我这辈子待的最久的一个地方。”
兰珍在心里捋了一下老太太提到的地名,好奇道:“芜湖——是一条湖吗?也是在大陆哦?”
“是安徽的一个小城,在长江下游,地方不大,现在晓得的人不多了,从前名气可不小,人家说我们那里是‘半城为山半城水’,不比苏杭差。”阿嬷望了一眼窗外一泓碧蓝的湖水,悠远地笑,“而且也是又出美食,又出美人的,大街上,小丫头们一个个皮子细得哟——元宵面一样。南京有‘金陵十景’,我们那里也有‘芜湖八景’的。对了,那时候,从南京一趟火车坐到我们那里,方便得不得了。”
兰珍“哦哦”应声,然后靠逻辑、不靠地理地把这几个地名在脑中迅速串起来:小蝶是安徽人,陈飒是南京人,她们以前提到过两个地方靠得近,那就是说芜湖和南京相隔也不远,近百年前就通火车也比较合理。阿嬷还一直讲“我们那里”“我们那里”的,她还估摸着那是老太太的故乡。
果然,阿嬷说:“我就是在芜湖出生长大、嫁人生子的,一直住到二十岁离开,再回去的时候家里人都不在咯,就剩了个四十多岁的侄女儿,孤苦伶仃的一个人。”她扭过头去朝徐姐和南希的桌子看了一眼。
兰珍听了心里有些难过,也顺着她的视线瞅了一眼徐姐,然后在心里粗算了一下,问:“那您二十岁以后再没回去——是因为战争的原因吗?我的历史不是很好。”她带歉笑。
阿嬷的脸上划过一丝落寞,沉默片刻,方缓缓地摇头道:“不是的,是我大大不让我回去。”见兰珍脸上似有不解,她注解,“就是我父亲,我们那里喊‘大大’。我前头嫁的那个人打仗打死了,我带着儿子跟了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连个名分都没有——我大大妈妈(爸爸妈妈)都不要我了。”
兰珍搭讪着喝了一口茶,旧时代的事她也不好置喙什么。
老人一打开了话匣子,就收不住似的:“我十七岁结婚,十九岁守寡,不上一年,就跟了个有权势的老头子。人家都当我是年轻守不住,又贪图富贵。其实,你说我一个年轻轻的寡妇,还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婆家不要我吃闲饭,我也不能赖在娘家。我虽然读过两年书,认得几个字,但并没有多少职业可以选,就找得到事做,也不够我养家的。我没别的路可以走,再往下走,只能比这条路更下贱。我的儿子,我不但要叫他活下去,我还要让他活得体面,所以我那时候也是没了法子,才跟了先勇他爷爷。”老太太的声音已经有些哽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