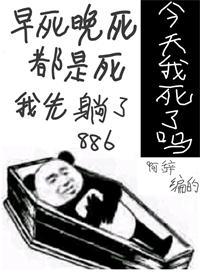52格格党>[穿书]反派boss上位指南 > 160180(第14页)
160180(第14页)
于是我看着我哥生生被大师兄打了十下,在雪地里滚了两滚,又将他拖回了屋里。
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大师兄只指着我的鼻子说,闭嘴,再哭就再揍你哥一次。
于是我终于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从此再也不敢发声哭泣了。
我哥告诉我,不许把今天的事告诉长老。
我想不通,明明长老会为我们撑腰,凭什么要忍着挨打呢!
我第一次跟我哥大吵。
我哥却扶住我的肩膀,紧紧盯着我。
他说:“不要再去找他们,在这里,我们才是外人。”
他说,没有人会为一个不中用的废物去惩罚天之骄子。
他说,去求他们只会得到同情和怜悯,却得不到正义和尊严。
他说,这样的友好,我们不需要。
从那以后,我跟哥更加卖力地去砍柴,捡松子,套兔子。
没人再来过,因为我不爱哭了。
没人注意我们,因为我们从不跟外人交谈。
我们是这座雪山上的灵,无人在意的时候,就像漂浮的空气。
在一个天不那么冷的日子里,远处的宫殿天空忽然爆发出绚烂的极光。
左右人都兴奋大喊:“华阳君出关啦!”
这是我第二次听到的名字。
那时我已经能区分人名。
过几天后,一个高大的男人经过禁林,远远地看过来一眼,又在众人的簇拥中离去。
只这一眼,我跟哥哥便得以识字断文,握枪拿剑。
我选习了药房长老的课程。
她在药田中侍弄花草,一把小小的锄头上沾染些泥土,她还记得我。
她问我们最近过得好吗?
我答,过得很好。
她说,很少有人选习她的课程的,我为什么选这个呢?
我说,剑术老师说我根骨不佳,难成大器,应该早做别的打算。
“所以,”她眼中隐隐透着兴奋,“我终于也要有自己的亲传弟子啦!”
我骗了她,我哥上了剑术课之后,身上莫名多了很多划痕,他疼的晚上睡不着,我也睡不着。
剑术课不是什么好东西,我想。
成为药房长老的亲传弟子,我可以光明正大地不去上课,我花好多时间跟师父识别草药,炼制丹药。
于是我的哥哥得以安眠。
可师父让我搬去她那里住,没有我哥陪着,我好久才习惯独自入眠。
我再不能与我哥形影不离了。
算来算去,只有初级典籍课我们会在一起修习。
他念:“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
我答:“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
我哥便笑:“是我太偏执,还是你太豁达?”
我摇摇头,我也不知道。
大师兄扛着剑从我们身边路过,轻嗤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