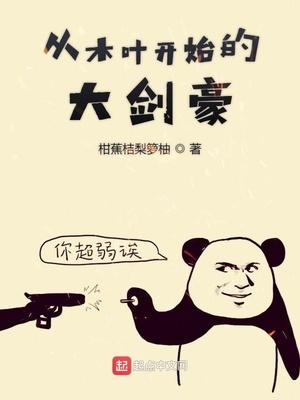52格格党>病弱美人是团宠 > 2530(第8页)
2530(第8页)
不不不,应该不可能。
这念头一起,张秀自己倒是先否定了,他总觉得纪昭不像是会和旁人走得这样近的人,更不会让旁人有机会把东西偷偷放在他的课业里。
再说了,没准是王猛看错了也说不定。
他正胡乱想着,桌沿上忽然被人敲了两下,张秀一个激灵,一抬头就看见夫子正在自己旁边站着,他当即吓得冒出冷汗,攥紧了手中的纸团,一时之间一句话也说不出。
“可是身体不适?”
瞧着眼前学生面上惨白的模样,夫子微微皱眉。
“没,没有。”张秀忙磕磕绊绊回道。
“若有不适莫要强撑,”瞧见张秀眼圈周围泛着的青黑,又思及这个学生的性子,夫子暗中叹了口气,“晚上切莫贪黑,早些就寝才是。”
“啊?奥奥,学生,学生知晓了!”
张秀忙不迭保证道,心里忍不住有些叫苦,他平日里其实一向都是睡得极早的,但是昨日从纪府回去后,硬是写课业写到了深夜,反反复复修修改改写了许多遍都觉得不满意。
他总疑心是自己没领会到夫子所布置的文题的真正含义,既然纪昭都说不简单了,那这文题肯定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
一定还有什么他没找到的更深层次的角度!
他就这样,写了几句又撕掉重写,来来回回竟从白日写到了半宿,最后梦里都还在写,好在最后总算是写出了还算满意的出来。
想到这里,张秀略微松了口气,但这口气还没松完,便瞧见夫子将自己交上去的课业重新放在了自己面前,
“你且讲一讲你的破题思路。”
摸不准夫子是何意思,张秀尽力回忆自己昨日下笔时时如何想的,断断续续才讲了几句,余光瞧见夫子隐隐摇了摇头,当下心里一凉,头脑一片空白,“夫子,我——我——”
……
好不容易熬到早读课下课,夫子一出去,班里的人立马凑成了好几团,来来回回议论不止。
潘小柳很想过来向纪昭讨要那张纸瞧瞧,但是站起身来后又没了胆子,硬是将张秀从凳子上拖起一块拉了过来壮胆,“咳咳,纪昭——咳咳——”
纪昭抬眸看去,“有何事?”
他脸色过于平静,看不出丝毫异样,潘小柳一时小小地梗了下,暗中将搭在张秀肩膀上的手向下压了压,用眼神示意张秀来开口。
张秀还处于夫子说他“想得太多,偏题严重”的话中,被他示意多次,才恍惚明白是个什么事,只是他本就不大相信这个事,更是不可能问得出口,因此犹豫再三,还是压低声音劝着潘小柳道,
“这事没准是个误会,还是别问了,快走吧,等会儿夫子要来了…
銥誮
…”
“你这么着急干什么?等下,我再去找王猛问问……”
瞧见两人拉拉扯扯地走了,纪昭无视周围若有若无的视线,重新将注意力放到了眼前的书本上。
只是目光瞥见书本边上露出的纸张的一角时,却不由得微微停顿了下,眸子中露出隐约的几分好笑来。
——怪不得昨日招呼也不打一声就走了,原是偷偷藏了东西在课业里面。
他想起昨日小姑娘哭得眼睛通红的模样,神色又是一怔,但转念一想,这乌龟她画也画了,人骂也骂了,这下脾气总该发完了吧?
正想着,忽听见门口有人喊,“纪昭,你家里人来给你送东西,现在人就在大院门口等你!”
家里人?
纪昭起初还当是盘豆有什么急事找了过来,但到了门口才发现是个面生的小厮。
这小厮明显也不认得他,一见他出来,先是确认了遍名字,才迅速将手中的东西递过来,然后含糊输了句什么家里给的就立马走了。
门亭檐下,纪昭看着手中的一团东西,眉头微皱,直到揭开最外面包着的一层废纸隐约瞧见里面纸团上的笔迹时,不知想起了什么,手下才加快了速度。
但将这团皱巴巴的纸张全部展开看清里面的内容时,纪昭面上仍是错愕了一瞬,眼中惊讶过后闪过一丝好笑,她这是以为这样自己就猜不出是谁送过来的吗?
轮值守院的学监本正坐在亭中案前张望着学堂的各处情形,此时瞧见纪昭这模样,倒是不由得有些好奇,向前探了探身子,“莫不是家中传来了什么好消息?”
纪昭摇摇头,在学监瞧见纸上字迹之前便已经将纸重新折好放进袖袋。
……
直到小绫悄悄儿来说纸团已经送到了纪昭手里时,阿意才稍稍地放松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