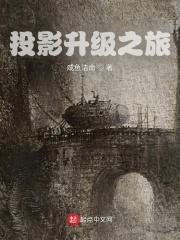52格格党>娘娘千岁 > 第116章(第1页)
第116章(第1页)
“宋尚书,你觉得如何?”宋璞玉是犯官、是囚徒,他没得选择。他又是个不甘于折腰的性子,想必会一口气答应下来。竹编笼里的雄鸡开始喔喔打鸣,刺得耳朵发疼。以芙捂住怦怦跳动的心口,忽然产生了个想法。褚洲侧目,沉默地看着她拭汗又皱眉。于是揽过她的肩膀,语气中暗含警告,“倘若要昏倒了,那就等你醒了再比试。”“奴家肚子里还有孩子,你们这样打打杀杀的总是对孩子不好。”以芙拉拉他的手,“你不顾着肚子里的孩子,总看在奴家的份儿上吧。”以芙知道自己的身子康健。虽然她现在还未与阿兄相认,但吃了太医院送来的药物后,肚子里的孩子始终安分。实在没办法了只能拿孩子作借口。“是我欠考虑了。”褚洲若有所思地摩挲着下颌,“不如让奴才把你带到卧室里,每回比试的结果都让下人捎给你。”以芙咂舌。她还不如在这里呆着。褚洲眺目,看了雪地中涩抖的宋璞玉,道,“雀雀时常以‘英明’誉我,我自然也不会让宋尚书白白地受了委屈。笼里的鸡就先由你挑选罢。”竹编笼里闹闹腾腾。斗鸡也分上等鸡与下等鸡。为了避免同类纷争,每一只雄气赳赳的雄鸡都各自分装在几个笼里。上等鸡挥羽邀风,悍目发光;下等鸡则是羽毛松散、长冠歪斜。宋璞玉指了指其中一个笼子。“想不到宋尚书一心扑在书上,择选鸡种的眼神却是不错的。”褚洲环住以芙的身子,告诉她那是洛阳城中最负盛名的“寿光鸡”,又让她也给自己挑一只。为了避免误伤到这位小妇人,旁边还有两个驯鸡的小厮紧紧地护在身后。以芙知道自己拗不过褚洲,最终还是走到鸡笼前。身后一人道,“姑娘右脚边的第二只笼里的鸡种是最好的,在今年的斗鸡比赛中可没输过。姑娘选了这个,大人会高兴。”以芙一眼也没往那边瞧,“哪只鸡是连战连败,在今年的比试里一次都没赢过的?”小厮也不知她为什么会这么问,只当她是纯属好奇,于是伸手指了指另一个摆得偏僻的鸡笼,“那就是了。”不同别的雄鸡在喔喔鸣叫,这是明显肥胖的斗鸡正缩头缩脑地把脖子藏在黯淡的羽毛下,连鸡冠子都发着白。小厮把它放在地上的时候,半跛的一只脚在着地的时候趔趄一下。以芙笑笑,“就它了。”“姑娘选它着实不妥……”“大人让我来选,可让你多嘴了?”小厮呐呐不语,神色仓皇地把那只死气沉沉的斗鸡提到了褚洲的面前,“这是姑娘为大人选的鸡。”褚洲眼中噙笑,扫了她一眼。“世上中看不中用的东西多了,那些人岂能因为一只鸡的外观,否定了它的实力?”以芙振振有词,“宋尚书挑的虽然威风,可却不一定实用啊。”褚洲看起来不像是生气,反而把她的身子圈在了怀里,“那你同我好好说说,我是中看不中用呢,还是中用不中看?”以芙愣了愣,没反应过来。他已经命人把鸡放入栅栏中,沉目去看。当地人好斗鸡,且寿光鸡这一鸡种十分名贵。毛疏而短、头竖且小、足直而大、目深且皮厚,一如赛场便开始挥动紫翅,长啸破云。反观褚洲的这一只斗鸡,还病恹恹地瘫在地上,对渐渐逼近的危险毫无知觉。院里的奴才常常去闹市里观斗鸡,知道自家主子已经没了胜算。偏偏他还气定神闲地坐于檀木椅上,仿佛输的人不是自己。第一回,褚洲败。“我要你辞官,说出做过的丑恶之事。”褚洲慢悠悠地应允,“成。”那只皮开肉绽的病鸡被人带了下去。以芙捏了捏手中的帕子,问还需不需要替他挑选。他勾了勾嘴角,“行。”鸡笼里的鸡再怎么挑,以芙也不可能找出一只和原来差不多的病弱斗鸡了。她左看右看,选了一只下等鸡。毫无意外地,褚洲再败。“我要你离开芙儿,和她再无瓜葛。”“你怎么知道是我离不开她,而非她离不开我呢。”褚洲握住以芙的柔荑,眉宇中闪过一丝挑衅,“雀雀,你说呢。”以芙还有许多事依傍着他,自然不会拂了他的脸面。于是低声,“是我离不开你。”褚洲看向宋璞玉,“听明白了?”“若不是你胁迫于她,她定然不能说出这样一番话。你只管告诉我,你是否能应下?”褚洲眼中已有冷厉之色,还是点头。第三回是最后一轮比赛,褚洲让驯鸡的小厮挑了。只见场上沙土飞扬,半空中翻飞着五彩斑斓的翎毛,两只斗鸡竟然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