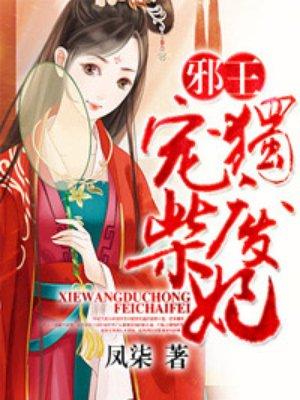52格格党>江国正清秋 > 第418章(第1页)
第418章(第1页)
采棠笑笑,候她脸色缓和下来,方道:“韩大人执拗性傲,却也不失为社稷臣。木有木的用处,钉有钉的用处,若因为钉子戳手就扔了,将来要用的时候,恐怕一时半会却找不回来。”
沈安颐扬眸向她看去,忽的莞尔。
“可惜本王不是个男子,否则便封你做王后,想必六宫清宁,家齐国治。”
采棠一笑俯首:“陛下说笑了。”
自然是说笑。采棠心里明白,就算陛下是男子,王后的位子也轮不着自己来坐。更何况伴君如伴虎,与其提着脑袋和三宫六院争风吃醋,她更愿找个一心人比翼颉颃,那些名位尊荣却是无所谓的。
正说话间,忽有内侍入殿。
“啓奏陛下,容国陆相国求见。”
沈安颐还未答话,便听采棠笑叱:“说什麽胡话?容国在哪儿?我们哪有个‘陆相国’?”
那内侍一愣,旋即反应过来,赶忙叩头:“是!奴婢失言!奴婢该死!”
“好了。”沈安颐挥手,“叫他进来吧。”
陆丛拜入殿来。
此前沈安颐只见过此人一回。彼时容国南部重镇已被昭国占领,容王委命陆丛前来临臯议和。国相为使,可谓隆礼,何况依着原本的计划,沈安颐也并未打算一口吞下整个容国,便许以罢兵,转而谋划对付连越。陆丛不知实际情由,见她答应得爽快,只当自家身价不菲,等到之后沈安颐欲取奚阳,与他通气时,便怕卖得贱了,于是有那一番游移摇摆的好戏,谁知竟惹恼了沈安颐,今日来觐见,便恭敬了十分。
沈安颐倚坐榻上,候他参拜完毕,笑道:“陆大人久见了。此番你助本王成此大功,本王真不知该如何谢你。”
她语气亲善,态度和豫,陆丛见状心下稍安,忙道:“这都是陛下英睿,算无遗策。臣岂敢当陛下之谢?雷霆雨露皆是君恩,臣能为陛下效力,实乃三生之幸。”
沈安颐打量着他,暗道此人虽是携贰之辈,说起话来倒着实顺耳,看这进退仪容,也真不失宰相风度,可惜是个靠不住的。她看看眼前人,想到韩子墨,心想这二人真是两个极端,要是能糅一糅就好了,既忠正又识趣,婉顺通变而又贞亮不移……当然了,世事难两全,很多时候只能取其一,能两全的都是稀世奇珍,历来少有,只好做梦去!想到此,心头蓦然一省:这样“糅出来的奇珍”,可不就是……
那个名字在她心间如一道飞光掠过,此刻毕竟无暇细想。陆丛的来意她心知肚明,无非是商量他的“酬劳”——对陆家等容国士族的处置。容国的土地好吞并,可容国那些大大小小的贵门却不好消化,昭国好不容易才变更了旧制,摆脱了士族门阀对朝政的把持,当然不能再走到回头路上去。
“容国才士济济,本王素有耳闻。”沈安颐缓缓道,“只是昭国自有用人之制,即便是本王,也不能罔顾国法。你可明白?”
“臣明白。”陆丛谦恭俯首,“入乡随俗,用人之事但凭陛下处分,臣等能得薄禄养身糊口,已是陛下天恩。只是另有一件,还望陛下恩準。”
“何事?”
“昔在容国时,已开士族入市之禁,他们之中颇有些人,做此经营已成风习,望陛下恩準他们照旧从事,不夺其资,不问其罪。”
沈安颐一想,这倒不算什麽大事,若是用一点市利就能将这些人安抚住,稳定朝局,却是桩便宜买卖。便笑道:“陆大人多虑了。只要他们安分守己,不干犯国纪王法,本王怎会夺资问罪呢?除此之外,本王还另有良田美宅赏赐于你,你可不要嫌本王小气。”
“臣不敢。”陆丛跪地叩首,“谢陛下恩典。”
数日之后又有边报送到,仍是昙林那边的麻烦事。眼下战火方熄,昭国元气未複,即便要收昙林,也得候过一段时间。便只令加强戒备,就近调拨了一支驻留容国的兵马以为援助。放下笔砚奏文,沈安颐合起眼皮躺进椅子里,觉得有点无聊。
想当初自己年少时,学习治国之道,倒新鲜有趣得很,虽有师长的期盼,却总不免带了点玩心。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事物不见得有多少差别,只是心境易换。
她睁开眼,看向御案的另一头,那里搁着几本旧书,原是拿来放在手边解乏消閑,奈何杂事太多,已许久不曾碰过了。
她翻开书,指尖触碰,是记忆中熟悉的质感。页角微黄,映在同样泛黄的灯火下,却也体味不出多少陈年旧韵。视线上移,行行墨迹间,题写着俊秀的小字。彤管细毫,是谁留下的笺注?芳言清语,是谁落下的眉批?
她的心潮顿时涌动了,说不清是高兴,还是伤感。一面觉得很快乐——挑灯对案,千里同心,书墨如新,十载共情……这是怎样的君臣知己呵?得此一人足慰平生。一面又觉得难过——那同窗课字,共研经史的日子一去不返,她只能对字徒叹,对书吊影罢了。
她轻轻擡手,茫然地撑住额头。良久,她放下书卷。
“来人。”
内侍应声而入:“陛下。”
“给我备马,要最快的。”
“是。”
烛花毕剥绽开,红焰微微一抖。夜风过窗来,拂落满卷思绪。
江山有岁序,尘劳无尽时,总有挑不完的重担,总有断不尽的公案。但在这月白风清的夜晚,我唯一想做的事,只是见你一面。
一夕明月,无边夜云。
万里长风越山度水,穿林打叶,惊栖鸟,过曲巷,涉清溪,踏琼瑶,萦回云际,飘降天阶,终于落定在小园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