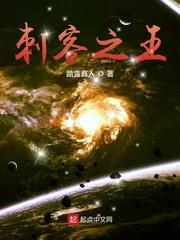52格格党>请和我结婚 > 7080(第18页)
7080(第18页)
双手忍不住颤抖,这是她之前在浴室看到的——倍力乐包装!
紫色的包装以及熟悉的图案。
根本不是什么面膜,而是指套。
江怡急切地从里面拆开,只剩下一个,其他的都不见了。
她几乎是下一秒就想到了她房里的几只指套,恐怕也是来源于这个盒子。
江怡感到非常疑惑,她觉得自己现在进入了一个看不清不知发展方向的迷宫里,踏出的每一步路都被人洞察预料。
她只能牢牢抓紧这个盒子,抓住这个线索,她要问个清楚。
为什么要在她房里放这种东西?
如果是别人放的,她兴许还会以为是变态,是为了寻求刺激,或是故意恶心自己,可若是钟彦伶女士放的,绝不可能会那么简单。
江怡把这个盒子放到钟彦伶面前,质问道,“我房里的指套也是你放的?为什么要这么做?”
“当然是为了帮她一把。”
又是这个回答,江怡忍不住大声吼,“这次你要帮谁?!你到底想做什么?”
许是大动肝火引得她好一阵咳嗽,脸色更苍白了一些。
钟彦伶似乎对她的大吼大叫感到不悦,但看到她虚弱惨淡的表情,许是不忍,盯了她好一会才缓缓道,“除了那个把我拉下台的沈司云还能有谁?”
“我不明白,你恨她,却在我房里放指套?”江怡跟不上她的思路。
“但是她的心魔是你。”钟彦伶一语中的,“江怡,从你答应借钱给司芸治病那刻起,你就逃不掉了。”
“我了解她,她对感情的忠诚看得很重,眼里揉不得砂砾。你借钱给司芸治眼睛,她在心里就已经开始怀疑你对承认她与你的订婚礼是一场欺骗,认为你是为了救下司芸而不得不委曲求全。所以我只需要再轻轻推她一把,她就会做出让人所不能容忍的出格的事。”
江怡隐隐猜测到这个“轻轻一推”是怎么个推法,喉咙一紧,不可置信问,“你把指套放在我房里,是为了让她误以为我和司芸发生了关系对吗?”
钟彦伶不可置否地沉默,过了片刻才又嗤笑道,“她知道后为了压制这份嫉妒和愤怒,她天天待在茶室修身养性,打磨性子,她以前鲜少喝茶,但她爷爷曾教过她品茶能养性,实在不行就抄经书,你看她茶具摔烂了多少套,经书抄了多少本,她本质上还是会介意。”
江怡跌坐在椅子上,血色尽失,“原来从我和你见面的那天开始,我就入了你的局……”
先是为了促进她答应做沈司芸的未婚妻,现在又是为了刺激沈司云而利用自己。
这个女人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怪不得她会说一见到自己就有种舒服的感觉,对于她这种人,一颗有用的棋子比亲女儿都来得顺手。
“不错,我也不怕告诉你,这些指套不止你房内有。”钟彦伶朝她浅浅一笑,“想知道吗?”
江怡双唇颤栗,下意识捂住耳朵,“我不要听。”
“在一楼的浴室垃圾桶里,那时你房里刚好蓬头损坏不得不下来洗漱,在你走后我顺势放了几只,你不知道的是你走后,沈司云下来过,我不知道她有没有看到,但那些誊抄经书的誊本字迹逐渐潦草就知道她看到了,而且心性还为此受到影响。”
“除此之外,她那死去的爹书房里也有,不巧的是你和司芸也在里面单独待过,她的心魔慢慢压不住了,从一开始地品茶养性,誊抄经书,到最后戴佛珠……”
江怡耳朵轰鸣,脑海里闪过沈司云扔到佛珠,残忍撕开表象告诉她被沈司芸看戏的一幕。
是不是在沈司云看到指套那些瞬间,她都会反复臆测自己和她妹妹放得多开,做得多激烈?
所以茶具才会越摔越多,经书越抄越潦草,最后抓住救命稻草一般戴佛珠。
沈司云内心就算再强大,也禁不住被她妈这么反复折磨。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江怡如坠冰窟,忍住了巨大的惧意才问出这么一句,“钟阿姨,你还是人吗?你配做她们的母亲吗?”
哪个母亲会把折磨亲生女儿当作乐趣,并且丝毫不觉愧疚?
不知是不是这一句惹恼了钟彦伶,嘭的一声,一个茶杯被她猛地摔到地上,顿时四分五裂。
江怡心尖骤然一颤,呼吸一紧,“我们三个人被你玩弄于股掌之中。”
“没有人可以压我一头,哪怕是我女儿也不行!”钟彦伶眼神凌厉,“嘉誉被她夺回去后,她禁足我只能在这破屋里活动,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不是犯人,她却待我如阶下囚!这就是我的好女儿。”
“钟阿姨,我再问一句,当初沈司云爸爸去世时,你建议我带奶奶去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提起?”江怡脸色发白望着她。
钟彦伶蔑笑,“你说呢,不这么做,你怎么会和我们站在同一阵线上?不断了你和她之间的所有可能,你又怎会心甘情愿做司芸未婚妻?她对你的恨又怎会深切至此?”
“钟阿姨,你简直病入膏肓!”江怡这才领略到面前人的可怕之意,根本算无遗策,任何人任何事都在她算计之内,没有谁可以逃得过。
“你觉得沈司云背叛了你,觉得她站在了你憎恨的伯父那边,所以你对她进行二十多年的布局和报复,甚至在她拿回嘉誉后还要刺激她折磨她,你有没有……哪怕一丝的愧疚,钟阿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