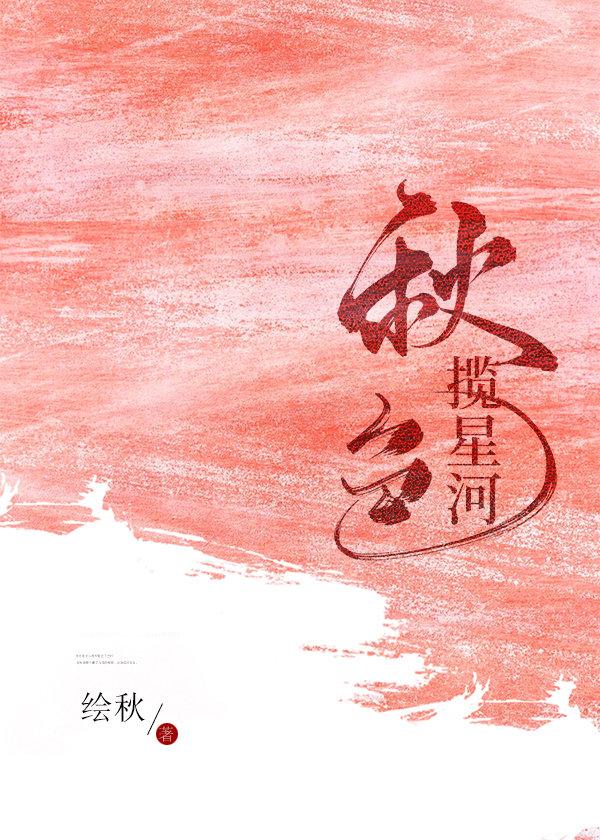52格格党>偏执驸马每天都在黑化 > 第64章 筹谋双更(第1页)
第64章 筹谋双更(第1页)
宁扶疏今日格外疯狂。
往常是盈着泪花说不要了,这晌是掉着眼泪叫他别停。
长榻薄衾皱得一塌糊涂,桌案书籍悉数被拂到地上,靠墙书架咯吱作响闹了整个下午。
精疲力竭的人汗涔涔趴在顾钦辞胸口,眼眶内雾气未散,眼神却无比清澈。须臾间,方才的情动恍如销声匿迹般不复存在。
她扯着喑哑的嗓子道:“横渠,你当日那般恨我恨陛下,为何没有杀了我篡位?”
顾钦辞揉着她的脑袋,将她浸润汗液的发丝一绺绺缕顺:“顾家军驻扎在北地,与金陵相隔甚远。一路向南攻城,双方难免死伤惨重,还会有数多百姓迫于朝廷政令应征入伍。”
他在战场上见惯尸骨成山、血流成河,反而更加厌恶生灵涂炭。
“又想着我如果反了,名不正言不顺,落在世人眼里就是个谋权篡位的乱臣贼子。我背上这个臭名没什么,但父亲、兄长,还有边关三十万顾家军,他们一辈子为大楚肝脑涂地的忠名不能毁。”
宁扶疏点点头,这确实是顾钦辞的性子:“除了这些呢?”
“后来有一段时间,舍不得对你下手。”顾钦辞挑唇道,“这条算吗?”
“当然算。”宁扶疏忽而露出轻笑。
顾钦辞扯了扯她滑落肩头的薄衫,遮住一片风光:“怎么想起问这个?”
“没什么。”宁扶疏任由他摆布,随口道,“只是突然在想,那晚踩芝麻杆,应该讨个升官发财好兆头的。”
说完这句话,她累得闭上了眼睛,呼吸很快绵长起来。
千里莺啼,杨柳映江。
关不住的满园春色中,和风一日暖过一日。郊外山花绽开得烂漫,正是踏青游玩的好时节。
这些时日,顾钦辞几次想带宁扶疏去城外山上赏桃花,但都被对方用各种借口回绝。
好似自那日酣畅淋漓地放纵之后,宁扶疏独自待在书房的时间,比以往多了好几倍。
像是又回到了曾经在金陵的日子,她总有批阅不完的奏折,处理不完的公务。
顾钦辞每回推门进去,宁扶疏无不在看各地影卫传上来的信报,其中又犹属金陵密报最多。叫人不禁怀疑,朝堂上出事了。
而当他询问宁扶疏,得到的回答永远是四个字:你别多想。
她只不过在思量一件棘手的麻烦,左右两条路都不好走,难以抉择。等她下定决心了,自然会将来龙去脉全部告诉顾钦辞。
顾钦辞离开后,宁扶疏唤来琳絮,头也不抬地问道:“西院那边,最近有什么动静?”
西院住着的是宋谪业。
“不安分。”琳絮总结出简短三个字,“往南飞的信鸽被咱们截下来好几次,回回都把殿下做的每一件事写得一清二楚。”
“如果只是这些也就罢了,更有甚者,自从殿下把绸缎庄的生意交给他后,他就开始借此接近罗姑娘,然后利用罗姑娘在各处生意场上的人脉,搭上了两条贩卖盐引和军马的线。”
“殿下,咱要不要把他……”琳絮眼底划过一抹精光,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休要打草惊蛇。”宁扶疏淡淡瞥她一眼,“假装咱们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盐引和军马随便他买卖,还有他放出来的信鸽,从今天起也不用拦了。”
“殿下——”琳絮闻言瞬间急了,忍不住道,“您明知他是陛下派来盯着您的人,为何要放任他胡作非为?贩卖盐引和军马是重罪,如果东窗事发,咱们可讨不着好。”
“慌什么,本宫话还没说完。”宁扶疏悠闲地抿了口温茶,是今春新出的明前龙井,入喉清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