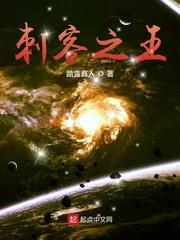52格格党>四爷怎么可能不做皇帝(清穿) > 第173章 第 173 章(第8页)
第173章 第 173 章(第8页)
他在四爷后边走着,心里一直琢磨:唉,这顿训挨得实在委屈。此次回京一路上听得都是皇家兄弟情深的故事。真实情况,自己还能不知道吗?那天碰上几位爷,被硬拉着去三爷府上坐了一会儿,无非是划拳吃酒说了些闲话。年羹尧和四爷的关系,不论哪位爷有机密的话,也不敢说给他听啊!好嘛,四爷可吃醋了。
年羹尧心里清楚,对四爷刚才的训斥,他也不敢说委屈。反正他年羹尧认了这么一个主子,也是命运的捉弄了,掰不开分不开了。灵答应当年的事儿,年羹尧隐约也有耳闻。他知道,四爷收留灵答应是担着天大责任。可是,四爷没有背着他,听说灵答应上吊,不是叫自己也跟着进来了吗?咳,到底是四爷重情义,发作完了,还照样宠着,信任着。年羹尧正在胡思乱想,不觉已经来到花园小佛堂了。
管家金常明正在门口站着,见四爷他们过来连忙上前说:“四爷,年大人,请到里边吧。”
四爷冷冷地瞟了一眼金常明说:“什么年大人。他和你们一样,都是爷的奴才。”年羹尧听了没有生气,却向金常明扮了一个鬼脸,悄悄地笑了。他知道,冲这句话,四爷原谅他了。
四爷阴沉着脸,来到灵答应住的房间里。尸体已经放到了灵床上,脸上盖着一张麻纸。四爷掀开看了一下,又盖上了。灵答应为什么要自尽?侍候灵答应的几个丫头只顾着哭,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四爷又把老疙瘩叫来。
金常明几步到门前,扶着哭得泪人似的老疙瘩进来,一边让他坐了,说道:“你先别伤心,慢慢说……”
老疙瘩低垂着头,苍白的头发丝丝颤动,声音嘶哑哽咽,本来已经弓了的腰深深弯着,抽泣着摇头,断断续续道:“……我……我也不明白她……怎么走短路……”他一头哭一头说,半晌,众人才知道,今天下午灵答应还好好的,因写字的宣纸用完了,叫老疙瘩去琉璃厂买。老疙瘩回来,说了几句话出去了,再见灵答应身体都硬了。他语无伦次地哭诉,索性放了声儿:“……可怜人要可怜可怜人……呜……我的二爷啊,我可怎么见你啊……”看着他脸上纵横的老泪,听着他撕心裂肺的号啕,人人心里发瘆,身上起栗。
“老人家,人死不能复生。”年羹尧沉思着道,“她都问了你些什么话?”
“她问的不多,只问了外头有什么传言。”老疙瘩哭泣道,“我没听说什么。我说前线打仗,豆子都征了军用,豆汁儿也涨价了。还听人传言,二爷本来有机会出来,叫一个姓贺的给卖了……”
年羹尧眼一亮,他已经若明若暗地知道了灵答应的死因。还要再问时,却见四爷苍白着脸,金常明刚说了句:“四爷,她是自觉没有希望——”四爷打断他的话,阴沉地点头道:“老疙瘩,她留下什么东西没有?”老疙瘩便回头看几个丫鬟。其中一个小丫鬟忙道:“奴婢惊糊涂了,是有一张纸在桌上,奴婢不识字,也不知写些什么。”说着将一张半尺幅的宣纸递过来。四爷接过看时,上头是一句话:
朔风冷淡旧亭台,又是一年寒意来。残魂那堪游人折,谁寻相思雪里埋?
篱下人绝笔寄雍亲王
邬思道转着轮椅过来,在四爷侧旁仰头看了,踅回去颓然坐了,半晌,说道:“这也算得殉节。其情可原,其志可悯。”
四爷慢慢将宣纸折起塞进袖里,两眼久久地望着烛光,良久,深深透了一口气,说道:“后事要好好发送。金常明明儿去法华寺请和尚,给她做七日水陆道场。”说罢便往外走,对一干下人道:“都散开去。”
“年羹尧,你先回去。明个下午,你到户部等着。金常明,你去叫大海大浪和前书房的几个小厮,立刻来如意斋。”
“嗻!”
年羹尧这回可真学乖了。下午是谁?一大早,年羹尧就骑着马来到户部,在书房里坐听招呼。哪知,他又失算了。整整等了一天,也没见四爷的影子。天傍晚了,户部的人全都要走了,四爷还不来。年羹尧正在着急,却见四爷府上的大浪跑了进来对赵申乔说:
“赵大人,四爷让小的给您传话。他今天在畅春园商议募捐的事情整整一天,乏了。请赵大人把今天的事情拟出个条陈来,四爷晚些时看。”转过身来,又悄悄地对年羹尧说:“快,四爷在门口等你呢!”
年羹尧小声问:“哎,我说大浪,你刚从南海来,北京熟悉吗就跑腿办事?”
大浪四下瞅瞅没有外人,悄声说:“先别问了,府里出大事了。我怎么不熟悉了?我也能做事……”话刚说一半,见门外四爷的轿子已经动了,便和年羹尧一起上马追了过去。
大轿在府门前停住,年羹尧急忙下马,上前打起轿帘。四爷看了他一眼,径自大步往里走。年羹尧不敢说话,急步跟上。一进二门,他就惊呆了:如意斋正厅里,府里十个管事都在,曲腰弓背,肃然而立,石头一般。四爷拉着年羹尧上来台阶,进来书房。弘曈给阿玛搬来椅子,放好垫子,请父亲坐着。众人一起磕头:“给四爷请安。”
四爷既不答活,也不让他们起来,却沉着脸说:“这几年,爷在外边的事情多,家里顾不上操心,让你们都受累了。皇父论功行赏,封了爷做亲王。爷呢,也不能亏待了你们。管账的在吗?”
一个五十多岁的老账房先生,连忙膝行上前:“奴才在。”
“上半年小汤山庄子收入多少银子?”
“回四爷,一共是一万四千一百一十八两。”
四爷微微一笑:“好。爷只要个零头过七夕节,其余的全赏出去。去几个人,把那一万两银子全抬到这里。”
老账房答应一声,带着二十几个伙计,到账房里抬出十口大箱子,一拉溜摆在长廊下。打开箱子,银灿灿,白亮亮的大银锭,映着满天夕阳红,直晃人的眼睛。
四爷瞟了一眼箱子,不屑地一笑说:“都看见了吗?银子确实是好东西。有了它,才有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好日子。但是,爷瞧不上它。爷看重的是人心、忠心。账房,你把这些银子分发下去。”
老账房答应一声,拿出一个大厚本子来说:“按四爷的吩咐,赏银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甲等五名,每人得八百两;乙等三人,每人得六百两;丙等四人,各得四百两;……这册子,是各房管事的轮流记录,经主子裁定的。”接着,便按名单依次颁赏。
四爷看看银子发光了,眯眼望着天边绚烂的火烧云,才说:“银子多少不等,拿得少的不需要抱怨。万事万物都有因果,忠、勤、慎,爷希望,各位都好生想想。为什么要重赏大海大浪?大海大浪来自南海,但是忠心办事,不会就学。爷不怕你们笨,爷不嫌弃你们笨。为什么没有大管家金常明的赏赐?金常明!”
四爷神色严峻。
冷漠沉静的目光看向在场的每一个人。所有人都沉默,脸上因为银子照耀的光芒逐渐褪去,恢复原本的皮肤的颜色。
“金常明,他是雍亲王府的管家,当年跟着朝鲜使团来大清,犯了事,被他上官污蔑打死了人,是四爷我念他家有老母,设法把他保了出来,从死罪到活罪,从囚犯又到家奴,一步一步,登上了管家的位置。爷本来还想要他出去做官儿,和戴铎一样。可是,他竟然为了八万两银子出卖了爷。尤其可恨的是,他伙同其他人害死了府里的其他人。金常明贪财卖主,坑害人命,这还能饶吗?”
金常明浑身筛糠,一个劲儿地在地上叩头:“爷饶命,都是奴才糊涂!”
四爷发出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冷笑:“……金常明,你不需要求爷饶命。你居然伙同奸佞小人偷盗变卖府里巨额财物,区区八万两银子就把爷卖了。你丧尽天良爷岂能饶你。来人!
几个彪兴侍卫应声而出,四爷吩咐一声:“拉走!”
众人一愣,四爷拉走金常明要做什么?可是,四爷的令旨,没有人敢问,更没有人敢不遵。侍卫再次动手,硬要拉走金常明。金常明面色灰败,四爷却望着天边的火红夕阳,说道:“好美的夕阳,可惜了。”突然,他转向金常明:“金常明,你有什么话说?
“主子爷,求您。可怜奴才还有八十岁的老娘,求四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