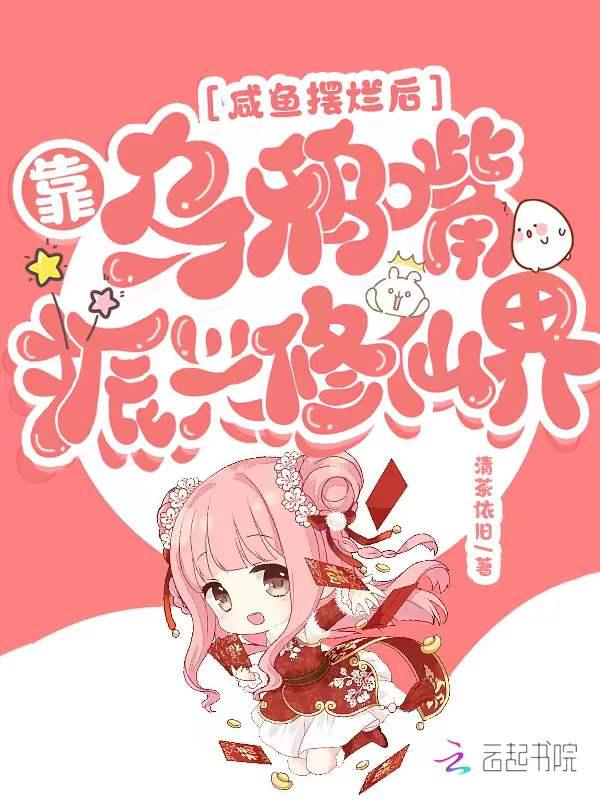52格格党>姜琬的古代科举青云之路 > 第 131 章(第2页)
第 131 章(第2页)
姜琬长长地松了口气,着人去柴房把离年带出来,那孩子已经冻的脸蛋发紫,险些死过去了。
“喝点热水。”姜琬把门关上,亲自给他弄了杯开水灌了下去:“下次喝酒,等我在家的时候再过瘾吧。”
离年用眼珠子瞪着他,缓过来后结巴:“我……这是要喝两口酒压惊。”
“你又没出府,何事吓着你了?”姜琬讶然。
离年有些无语:“五更有人翻墙来找你,我本想点他哑穴的,还没动手人就晕倒了……”
姜琬愕然:“什么人?”
离年摇头:“外面套着麻布衣衫,里面穿着下级武士的内衬,我推测,可能是个当兵的。”
“人在哪儿?”姜琬心上突地一跳。
离年:“我查看了他身上的伤,很是诡异,不敢声张出去,先藏在柴房后面了。”
姜琬骇道:“他进门的时候可有血迹留在身后?”
要是被人追杀的话,这雪天,红通通的血迹再醒目不过了。
“这倒没有。”离年摇头:“我出去查看过,咱们府周围方圆几公里之内都没有看得见的痕迹。”
姜琬皱眉,眼中的忧虑之色愈发浓厚:“你去挡着府里的人,我去瞧瞧。”
漫天飞雪迷人眼,一片han气透彻骨。
姜琬迎着风雨摸到柴房后头,扒开离年说的雪堆,果然瞧见一片土黄色的衣裳。
“秦真!”
姜琬低呼一声,脸变的比飞舞的雪色还白。
秦真已经冻僵了,动也不动,像死了一般。
姜琬赶紧把人挖出来,拖进柴房,用里面破旧的被褥盖上,跑回去取热水热炭。
等他返回来时,离年已经先进来了:“公子,您认识他?”
“你去取些我的棉衣来。”姜琬点点头:“再把我院里的人打发到老太太、夫人那儿去,等他醒了……”
自然不能躲在柴房的。
“是。”离年应声去了。
姜琬掰开秦真的嘴,给他灌了些热水,又把两床破旧被褥压得实沉些,自顾道:“大概边境上的事比想的要严重……”
“都死了……都死了……”也不知是不是为了回应姜琬,原先直挺挺躺在那儿的秦真忽然拧紧了眉,痛苦地嘟囔了句。
姜琬贴近他:“谁死了?”
他心中不详的预感愈来愈清晰。
秦真没回应他,又昏睡过去。
门微一响,姜琬回身,见是离年取了棉衣过来:“路上遇见人了吗?”
离年否认:“这么大雪的,谁出来。”
姜琬没说话,把炭盆挪近些,揭开被褥,刚想伸手去脱秦真的外衣,忽又缩了回来:“离年,还是你来吧。”
离年嘻嘻笑道:“公子这般人物,他哪儿配让您给他宽衣解带的。”
姜琬但笑不语。
离年利索地扒掉秦真身上乞丐不如的破烂外衫,正要往上套棉服,忽然触到他腰间硬硬的:“咦,公子,这是什么?”
姜琬凑过去,脸色一变:“取出来。”
他见那信笺没用兵部的官方信封,缄口处写了个宗府字样,立马接到手里,来不及多想,边往外走边嘱咐道:“你照料好他,我出去一下。”
朝廷有探子,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