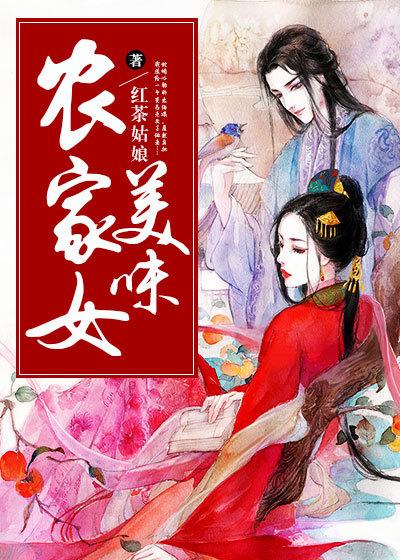52格格党>冬雪春风 > 番外一 从北大荒到上海滩1(第3页)
番外一 从北大荒到上海滩1(第3页)
二楼的面积非常狭小,还没有我们农场的家的一铺坑大。
左侧窗下摆着一张双人床,右侧有一张单人床,楼梯旁边的天花板上有一个大洞,一架梯子搭在洞口,那是通往阁楼的楼梯。
五六十岁的公婆和小姑子每天都要踩着梯子爬进去睡觉。
文白跟我说,一楼要兼做客厅餐厅,不适合我们。阁楼的地面有个大洞,怕阿竹不小心掉下来。所以,二楼是最合适的,他给我们争取到睡在二楼的机会。
天太热,阿竹睡得不安稳,总是哭叽叽地动来动去。
弟妹可能是怀孕的原因,一直叽哩哇啦地高一声低一声抱怨着。
楼上楼下,公公和大伯哥山一般的呼噜声相互应和。
然而这些
都没能影响我,三天的硬板坐下来,实在太累太困了,天大的事也等睡醒了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在各种嘈杂的声音中醒来。
当当当的闹钟声,上下楼梯的脚步声,外面叮叮当当的切菜声,大人吼孩子起床声,莫名其妙的争执声。
以前,叫我起床的是家里那只大公鸡。
我一时恍惚,不知身在何处。
“妈妈妈妈,尿哗哗!”阿竹突然从床上站起来,她要撒尿。
我慌忙把她抱起来往楼下走,公厕太远了,马桶在哪里?
我一边往楼下冲,一边东张西望找马桶。
突然,身上一热,阿竹尿了。
阿竹三岁了,已经懂得害羞。她哇哇大哭,而我则怔在当场。
文白正巧刚从外面回来,看到我们的样子,伸手把阿竹接过去,叫我一起上楼换衣服。
我昨天是合衣睡的,这套衣服在路上穿了三天,被汗湿了一遍又一遍,现在又被阿竹尿了。
绿色的衣裤洇湿一大片,变成墨绿色,无比刺眼。
我在众人的盯视下,尴尬地转身上楼换衣服。
可是,怎么换呢?
这屋子连扇门都没有,楼上楼下随时都可能有人进出。
文白给阿竹换了衣服,下楼一趟拿了锤子钉子回来,在墙和天花板上钉了几个钉子,从我们带来的行李里翻出一个大花被单挂了上去。
“好了,趁着没人,快换衣服吧。”文白冷静地说,“这没什么的,上海家家户户都这样,你要习惯。”
我背
转身去,强忍着泪意,迅速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
“先下楼吃饭。一会去水池那把衣服洗了。”文白催促道,“吃完饭,我要去学校报道。”
我们一家三口在上海的生活就从这样一个兵荒马乱的早晨开始了。
起初我以为我们家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万万没想到有些福气我消受不起。
一个月后,我毅然决然地带着阿竹独自返回了东北。
让阿竹三岁就没了爸爸,是我不好,但我从没后悔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