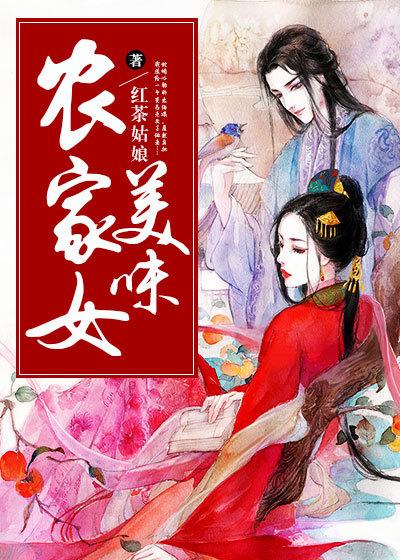52格格党>冬雪春风 > 番外一 从北大荒到上海滩1(第2页)
番外一 从北大荒到上海滩1(第2页)
我们一家三口的回归,令这幢本就狭小低矮的房子更加拥挤不堪,连转身的地方都没有。我简单吃了几口挂面,就领着阿竹出门透气。
上海的潮热令我几乎晕厥,滚烫的空气随着呼吸进入体内,我觉得自己就是热水里的一条鱼,就快要煮熟了。
周围的邻居见我和阿竹是生面孔,都过来搭话,又见阿竹生得可爱,不时有人伸手过来捏她的脸。
阿竹又惊又怕,躲在我怀里不敢抬头。
她的小褂子早已被汗浸透,湿漉漉的粘在身上。泪水和汗水把她的刘海粘在脸上,黑一道白一道的。
我只能使劲儿地摇着扇子给她扇风,可扇出来的都是热风。
“回家!回家!妈妈,咱们回家!”阿竹一直闹着要回家,她说的是回北大荒
农场那个家。
可是,从此以后,我们就要在这里过日子了,爸爸的家就是我们的家。
“乖,阿竹不哭,妈妈在呢。”我无力地安慰着。
平时只要文白在家,就是他看阿竹我干活。
他比我会哄孩子,阿竹也更跟他。
此时,他正在房间里跟公公婆婆他们商量着什么。我只好抱着女儿拍她睡觉。
路上的三天,孩子遭了大罪,累坏了,哭着哭着就睡着了。
天渐渐黑了,弄堂也安静下来,但文白始终没有出来叫我进屋,房间里不停地传来争吵声,我听不懂他们在吵什么,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吵完。
我抱着阿竹,靠着墙,打起了瞌睡。
不知什么时候,只觉手里一松,睁眼一看,原来是文白把阿竹抱了过去。
“跟我去上厕所,然后回屋睡觉。”
我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跟着他往公厕走去。
公厕里很黑,一个小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我小心翼翼地看着地面,生怕踩到什么,更怕踩空掉下去。
“妈妈,臭!”阿竹捂着鼻子,皱着眉头在我身上扭来扭去。
我哄着她上完厕所,把她抱出去交给文白,又冲回去解决自己的事情
绕过路两旁的杂物,低头躲过上面垂下来的衣服,一路曲曲折折地回了家。
我们的回归,给齐家人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之前,他们以为文白已经结婚生女,就在北大荒扎根了,不会再回上海。
家里上中下三间房子,大哥一家住一
楼,二哥一家住二楼,公婆和小姑子住阁楼。
突然回来的我们,打乱了原本的平衡。
鸽子笼一样的屋子,哪里都塞不下我们。
可总不能让我们睡大街吧。
经过一个晚上激烈的讨论,最终的决定是,二伯哥家的女儿惠敏去一楼跟堂姐惠捷挤一张单人床,她的床给我和阿竹睡,文白则在我们床边打地铺。
我跟着文白往屋里走,昏暗的灯光下,所有人的脸上都没有笑模样,惠捷惠敏姐俩更是气鼓鼓地瞪着我们,好像我们是强盗,抢了她们家的粮仓。
我假装看不见,踩着摇摇晃晃的木楼梯来到二楼。
木楼梯仅有一人宽,我尽量放轻脚步,可它还是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