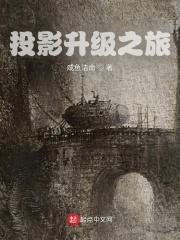52格格党>蒹葭 > 第 49 章(第3页)
第 49 章(第3页)
“是吗?因为什么呀?”婉清回头看了一眼,又问道。
“皮呀,东家挨完骂,西家挨,连皇后娘娘那么温良的人,都觉得她烦。而且她还偷偷往人饭里加墨汁,说什么这样肚子里墨水多……”
那都多会儿的事情了……越葭现在完全不想说话,翻了个白眼,准备离开。
刚走没两步,就被王嬷嬷拉到小角落里,她小声道:“下午有个叫银音的小娘子要见婉清,我没敢让她进来。”
越葭用余光瞥了一眼,思考片刻,回道:“我知道了,嬷嬷。”
王嬷嬷一脸心疼,语气复杂又带着些许愤怒道:“你不知道,她换衣服的时候,我刚好在场。那身上一道道,一片片的,我都没敢问。你说这么小的女娘,以后可怎么嫁人呀?唉,当真是禽兽不如。那些人就该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那嬷嬷有空就多宽慰一下,别让她想太多。”越葭打断道,并没有向她解释什么。
“那明日还需要继续看着她吗?”王嬷嬷又问道。
“不用管,我会派人盯着她的。”
这时,二人背后传来婉清声音,“郡主,我想问一下,我什么时候能离开?”
她见二人说起话来,看着像是一时半会儿都停不下来,便有些沉不住气地发问了。
“我觉得,我也不好一直住在郡主府上。更何况百花楼那边,我不在这两天,恐怕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下午的时候,银音娘子过来看你了。”越葭让王嬷嬷先下去,然后慢步走到婉清面前,“我既不会让你回去,也不会让你见银音的。”
婉清微怔,身体逐渐僵硬起来。
“说起来,我还挺佩服你的。”越葭绕过她,讥讽道,“但凡是能住在戚里的,哪一个不是被经营得固若金汤?随便盘问盘问,就清楚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你居然敢独身闯入乡侯府。还好也就是个没实权的乡侯,但凡要是换个地方,你早就身首异处了,怕是连个尸体都拼凑不全。”
婉清好半天没说话,直到越葭准备离开,她才红着眼睛,颤抖着吼道:“人微言轻,就该被随意乱杀吗?地位卑贱,就没有活下去的权利吗?”
面对眼前高高在上的郡主,她心里的愤怒再也压制不住。
她何尝不知戚里各家防守严密,可她有什么办法?如果不这么做,她又能做什么?难不成就让她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没有任何损失,一辈子荣华富贵?而自己视为再生父母的主事却面目全非地永眠于地底?
这让她怎能忍?
的确,在世家门阀割据的情况下,普通人别说是升官,就连活下去都是个问题。更大的问题是,皇帝潜邸时是借助世家的力量登上皇位的。如今再想动这帮世家,那几乎是登天之难。
面对这种复杂的情绪,越葭罕见地有些迷茫。她不再像刚刚在王成面前那样伶牙俐齿,而是相对地有些沉默。
这种沉默,更像是一种无言以对。
过了好久,她才说道:“你的确有活下去的权利,我也并非不让你去报仇。但在自己无法独善其身的情况下,做出打草惊蛇的举动,无疑是自己把自己往火坑里推。昨日的事情,你还没受到教训吗?”
婉清似是想起了昨日的侮辱,不禁有些羞愤地低下头,她的拳头攥得紧紧的,嘴唇也被咬出了血。
越葭觉得自己的话似乎有些重了,但她仍是威胁道:“总之,在我没忙完之前,你最好不要离开郡府。不然,我可不敢保证府里巡逻的赤甲军会不会把你扎成筛子。当然,你最好写信和那位银音小娘子交代清楚。这样,我就不用把她请到郡府来了。”
说罢,她径直向外走去。
看着那道冷漠的背影,婉清跌坐在地上,羽睫忽闪忽闪,随即两行清泪顺着脸颊流下。单薄的身体如同蝉翼,一碰就碎。
她坐了一会儿,缓缓从头上拔下簪子。绝望随着眼睛闭合,最后凝聚成一颗毅然决然的心,她猛地朝自己刺下去。
只是如期所致的疼痛却并没有到来,婉清立即睁开眼,愕然地看向不知何时返回的越葭。
只见她半跪着,手牢牢地握着那支差点要自己性命的簪子,接缝处不断地溢出鲜血,滴答滴答。
越葭走了一会儿后,觉得自己好像太过无情,便想解释解释。所以就又翻了回来,正好撞上这一幕。
她长长地吐了口气,将婉清的手指一根一根掰开,然后迅速将簪子扔了出去。
她莫名地有些来气,但最后还是平复了一下心情,尽量温言道:“若是因为前主事往日的恩情,你且放心,这事儿我不会不管的。但我最近很忙,所以要往后放一放。你要是觉得无聊,可以找王嬷嬷聊聊天,或者请银音小娘子过来坐一坐。但若是因为昨日在贺家所受的□□,我绝不阻拦你。只是我私以为,你最好还是报了仇再自杀,才更爽快些。”
她言尽于此,若是婉清再做出轻生的举动,她也不会再如刚刚那般费心费力地阻拦了。
婉清再抬起头时,越葭又只留下一个远去的背影。只是此时,她的情绪似乎缓和了一些。可眼泪却仍旧不受控制地缓缓滑下,在她苍白的脸上留下一道道痕迹来。
最终,泪滴砸向地面,留下一片污迹。
枯败的树在风中摇晃着,发出簌簌的响声。枝头上如墨般的鸦暗哑地叫了几声,黑漆漆的眼睛一眼望不到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