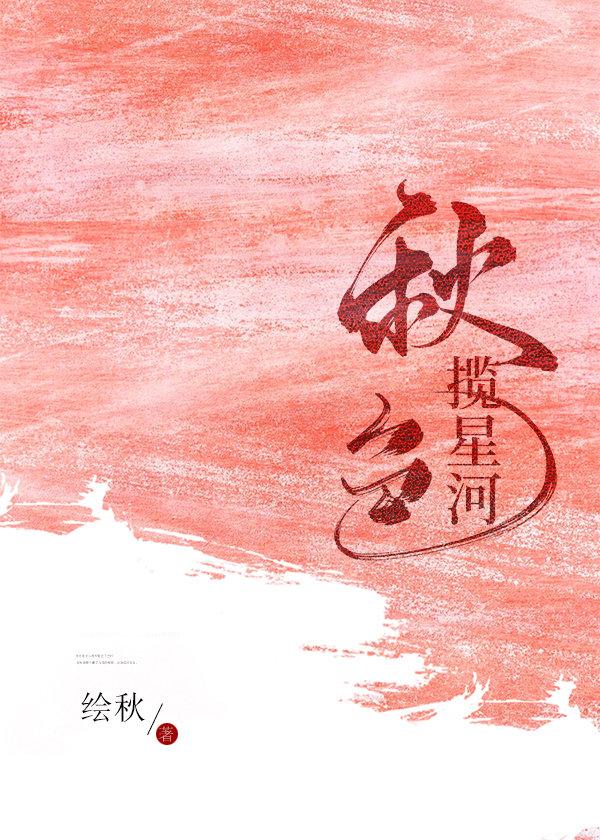52格格党>阿萝 > 第296章(第1页)
第296章(第1页)
可阿萝猜中了。与他附耳时,她赧着睫,字字笃定,说他志在千里、保准爱鹰,也说他不屈凡俗、定会为鹰解开枷锁。
她是世上最懂他的人,甚至远胜他自己。
思及此,魏玘目光愈缓。几时不见,他已十分想她,念她发香、丹唇,与柔软的心肠。
“哧!”兔子狠狠地踢他。
魏玘牙关一咬,黑着脸,把兔儿举回面前。
一时之间,浓赤与墨黑相对。朱红的兔眼好似明镜,照出咬牙切齿的一张俊脸。
“看什么?”魏玘不耐,“真当朕会喜欢你吗?”
兔子当然不会说话。它不知听懂多少,眼珠如凝,注向魏玘,寸步不肯退让。
魏玘凤眸微眯,读出一股似曾相识的执拗。
有时候,抑或是大多时候——某位漂亮、赤忱的小神女,也会这样盯他,用灼而清亮的眼,直将他的心烧出个洞来。
他的阿萝很像兔子吗?
像什么呢?像它温和、绵软、娇小,还是像它外柔内刚、时不时地瞪他一脚?
魏玘冷笑一声,心斥这比方荒谬至极。
“杜松。”
“听凭陛下吩咐。”
“你差人去一趟尚服局,命崔尚宫为它裁件新衣。”
“……为、为谁?”
“……”
“……微、微臣该死。微臣领命。”
……
越书记载,永徵十一年九月,昭仁公主赠兔于高宗。
高宗勃然大怒,封之为兔儿将,赐新衣一匹、萝卜三十两,尝抱兔伫立、观赏皇后画像,一并语云:此事不足为皇后道也。
第134章利断金
阿萝走出红墙时,漫野的星辉已开遍天帷。
清光如白练,柔柔洒落她两肩。她仰首,去瞧高悬的孤月。一袭银泥缬袄俄而攀来,受女官牵着,罩住她娇小的身子。
“多谢你。”她轻声道。
女官笑答折煞,福了礼,便退居一旁。
墙外的宫道寂而悠长,连通殿阁与掖庭,灯火炳如昼日,照出一方雕金凤轿。几位宫人候于轿旁,低眉垂目,静待皇后归殿。
多年来,如此景象司空见惯,阿萝却很难习以为常。
她自幼独居小院,尊卑观念薄淡,不论对谁都一视同仁。是以往常,瞧见这番情形,她定会上前致歉,道是自己耽搁拖延、害得几人好等。
可今夜,阿萝没有动。她只望着月,杏眸纹丝不移,纤影抹上光华,像融于墨里的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