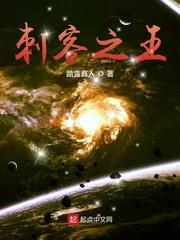52格格党>孤王有病 > 029(第2页)
029(第2页)
“小婢不敢冒然回京,但瑶光寺急信不可不传。”
阳阿冷道:“什么急信竟要你连夜回京。”
侍女不敢欺瞒,“瑶光寺宫监已经赶到前朝禀告,酉时三刻,寺中讣告,冯贵姬薨了。”
阳阿眼皮一跳,预感不祥,“庆阳知道了?”
“嬷嬷发觉时……贵姬的心腹早已逃脱。”侍女支吾着,“许是、许是知晓了。”
“知晓了?”阳阿微眯美眸,挑眉注视着地上抖如筛糠的侍女,“我说过,她死了不要紧,要是胆敢让她身边的人回来通风报信,必叫你不得好死。”
阳阿面色剧变,抬足重重踹在了侍女头上……
惊闻母亲病逝的噩耗时,庆阳正在姨母冯贵妃宫中抄写第二十九卷经文。
这是她每日功课,潜心抄写佛经,积攒功德,为母亲祈福,祈愿她病体早日康复。
只是今夜不知怎的心神不宁,始终静不下心来抄写,致使笔尖落下墨汁,污毁了经书。
保母劝道:“公主还是明日再写吧,一百卷一时半会也抄不完。”
庆阳醒过神,提笔继续,“要是半途而废,佛主会因我心不够诚而多加怪罪。”
见公主沉浸佛经,保母暗暗叹气,起身去备宵夜。
刚至殿前,隐隐瞧见贵妃身边的女官领着一名内侍匆忙而来。
待两人近了,保母才认出是贵姬身边的内监,不由大吃一惊,“宫监怎的来了?!”
庆阳立在案后,颤声道:“你怀中何物?”
宫监一摸衣襟,绢帛已然露出一角,随即再也控制不住,放声恸哭,“殿下请节哀。”
“阿娘的遗笔?她留给我的遗笔。”庆阳几乎咆哮,“快给我。”
宫监递上绢帛,“殿下珍重。”
庆阳充耳不闻,展开绢帛,双目逐渐通红,视线停留在“公主芳鉴,敬启者”几个字再也挪不开。
梗在心头的一口气是她忍受多年的委屈,这口气松了,就是要了她的命。
“阿娘!”
庆阳松手倒下,身后的屏风发出轰天巨响,在平静的晋宫惊起波澜。
小冯氏病薨的消息传开后的第三日,云州方向来了一位宫使。
宫使并没有大张旗鼓地觐见元玮,而是乔装成侍卫赶到国邸,将信件当面呈递给了破阵,请他转呈真珠,便仓促地离开。
信是太上皇写给真珠的亲笔,太上皇在信中写,已顺利到达离宫,又说起沛王身孕云云。
兰重益从外面回来,就见真珠面上带笑,“是有什么喜事么?”
真珠把信给兰重益,拉他坐到身旁,“四姊临产,君父很是担忧。”
兰重益展信览阅,真珠便偎在他肩头,“九娣近来哀思过甚,闭门谁也不见,四姊也好些日子不曾见了,上次见她心事重重,莫非是将为人母,心思郁结?”
兰重益笑道:“真珠若是做了母亲,可会因此悒郁?”
真珠愣住,前世应星和她并不亲近,久安又因兰重益之故不得她重视,可说那一生她都没有尽到半分母亲的责任。
真珠心怀愧疚,伏到兰重益耳边,“如果是和公子生,岂会悒郁。”
兰重益红了耳根,握拳抵唇咳嗽了几声,“君父说云州离宫没有黄梅。”
真珠道:“他最爱黄梅。每年春日开花,专门莳花的宫女便会剪下枝条秀美的送到内禁,翌日君父就把黄梅分赐给大臣,此后晋臣都以得到御赐黄梅为荣。”
兰重益把信拿开,抚上她的额头,“太医来问过脉了吗?怎么说?”